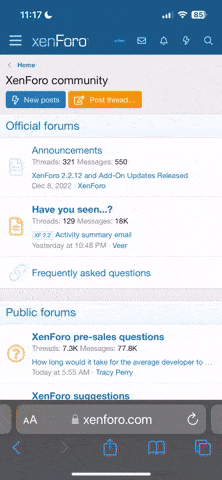榕树头下小子
小学三年级
- 注册
- 2006-03-30
- 帖子
- 234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1
冼氏墓及冼夫人故里----广东电白山兜丁村
作者:张慧谋
老家在小城南郊。城北十里外的山兜丁村,便是岭南“圣母”冼氏墓的所在地和冼夫人故里。
外人一直以为,山兜丁村同属一处,其实这是误解。冼氏“墓城”遗址在电白山兜,与之相隔三四里地的丁村,才是冼夫人故里。自古以来,山兜丁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故被人混为一谈。
甲申年农历正月廿五父亲忌日,我回了一趟故乡,顺便去了山兜丁村。村中几位长者,老早就在娘娘庙里等着我们。
看上去,娘娘庙虽然有些破败,但仍遗风犹存,古朴而庄重,不像一些新修的庙宇,大红大绿的俗气得很。娘娘庙后豁出一大片空地,约有五六十亩,茂草疏林,隋代瓦砾俯拾皆是,据说这里就是“隋谯国夫人冼氏墓”遗址。背驮墓碑的那块“?”(龟趺石),像一只千年老龟,闭目静卧,石质坚硬,乌黑发光,至今仍存于“墓城”内,即娘娘庙后。经专家鉴定“龟趺石”为隋物。有趣的是,五六十年代,此石一直遗弃路边,被上山砍柴的樵夫当“磨刀石”,石面的乌亮处,便是磨砍柴刀时留下的痕迹,也是无知和愚昧的反照。
村中长者说,娘娘庙原本是丁村冼氏的宗祠,为纪念先人冼夫人所建。如此说来,娘娘庙应是最早建的冼夫人庙了。建庙年代不详,一种说法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年),却有专家认为,这说法未必确切,况且志书上也没有记载。但今存于娘娘庙里的那只“虎头纹”香炉,属隋物无疑,这倒是实实在在的。
据道光《广东通志》记载:“高州电白县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碑失。嘉庆二十四知县特克星阿重立碑。”也就是说,我们现时所见的立在“墓城”遗址相思林中的那块墓碑,是后来知县特克星阿重立的,原碑已失。特克星阿从北方来电白做官,想不到他此举却为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寻的历史见证,至少可知隋“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的大体方位。
提及冼氏墓,村中的几位老人话语滔滔,他们似乎都有着满肚子说不完的故事。岁数最大的一位,已年过八旬,但老人的记性相当好。他说他小时候,不敢靠近“墓城”半步,偶尔经过这里,也是远远的、怯怯的看上一眼,就赶紧离开。那时的“墓城”有城墙、城河和城池,城墙高过人,城内阴森森的,据说里面还有守墓士兵居住的“兵房”遗址。照此说来,冼氏墓的面积不仅大,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我从一篇研究冼夫人文化的论文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冼夫人的爵位“从其夫”(即隋谯国公冯宝),也即是三品官衔以上,死事也是按此置办。冼夫人本身也受隋帝册封:宋康郡夫人、谯国夫人。并被授权:开幕户、置长史、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官行事。死后又谥为诚敬夫人。在当时,冼夫人的权力不仅是“听发部落六州兵马”那么简单,而且还拥有“先斩后奏”权。难怪南越王墓博物馆顾问、广东考古界老前辈麦英豪先生断言:“在岭南,除了南越王赵陀,惟有冼夫人这么高的封号才能相配。”
冼氏墓经历了1400多年沧桑,当年的辉煌不再,偌大的“墓城”遗物寥寥,但有些地段的城墙,仍是有迹可寻的。村中老人领着我一边走一边回忆,他们指指点点,这块凸起的地方就是老城墙,泥土夯实的,那边是城河,再远点长着竹子的地方是城池……总之,老人们像在向我打开一本纸质发黄的古书,让我阅读。可我却是茫然复茫然,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满地的老瓦片和荒草,我真的难以再看到什么。岁月就是这样的无情,再伟大的人物,与凡夫俗子无异,同样是时间的匆匆过客,顶多是在史册上留下一些苍白的文字,或与他生前有关的一些能引起人们对他们缅怀的史迹的印记,仅此而已。
我在“墓城”内默默地走着,不知哪一脚是现实,哪一脚是虚幻,仿佛我每一脚踏下去,都会惊动这位岭南“圣母”的酣梦,都会踏翻一些隋代的瓦当,甚至稍不小心,脚底还会被一枚陪葬的银器或金钗狠狠地扎一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早些年,就有村民在“墓城”里拾到金钗之类的陪葬物。“墓城”颇大,老人带着我从南转到北,又从东转向西,走着走着,额头就冒出细细的汗珠来。墓园内的相思树几乎是朝着一个方向斜斜地生长。晌午的阳光透过林木间,那些相思树,像在俯视,又像在倾听。四周静极了。
我内心一直在思忖着一个问题,偌大的“墓城”空留在村中央,四周都是村舍,竟然没人在这块“风水宝地”建房屋,甚至农作物也没有,就让它白白地空着这么多年,足足十多个世纪了。我问何故?老人说,这里是“冼太妈”(冼夫人)的地方,是块圣地呀。也许是出于后人对冼夫人的敬仰和崇拜吧,他们才会如此自觉地、默默地将“墓城”保护起来。老村长对我说了一件事。80年代初,有邻县人开着一辆汽车来山兜,想搬走那块“龟趺石”,被他和村民阻止了。不久,又有外地人想以六、七万元高价把“龟趺石”买走,同样被村民拒绝。由此可见,这里的村民对冼夫人文物的爱惜和保护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我提出要到丁村去走走。丁村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舍零散,几乎建在田地边。这里的田园没有庄稼,显得空旷而恬静。村边东头,有一座小山包,叫丁村岭仔,是隋朝留下的印记。1400多年前,冼夫人的故居就在这里,当地文物部门还在山脚下立了一块碑石:冼夫人故居遗址。
我一个人爬上山头,山顶平坦,有半个足球场大,据说这里是冼夫人习武之地。站在山顶眺望远处,周围都是一马平川的田野。北边的那座高山,是冼氏家族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据说山中还有三只“俚人洞”,洞的直径约3米左右,深度却无人知晓,因为从来没谁有胆量到洞中探个究竟。这三只神秘的洞穴,也是隋代遗留下来的,按专家的说法,“俚人洞”是俚族人躲避外来入侵者的地方。丁村的西南面还有一座小山包,当地人称这里叫“马场”,大概是马房或牧马之地。村边有一片约20余亩的农田,叫“妈田”。俚语“妈”即汉语“婆婆”的意思。“妈田”即冼夫人名份下的田地。冼夫人故居遗址,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草丛里偶尔露出一些厚厚的瓦片,这些不显眼的隋代瓦片已有1400多年历史。要不是阅读碑上的文字,谁会想得到,这地方曾出过一个权力可与南越王赵陀匹故、受到三朝皇帝册封的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今天的丁村村民没有一个是冼姓的后代,都是黄氏家族。何故?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隋唐之交,冼氏家庭倾巢迁徙海南,搬迁的原因有不同版本,一说法是冼夫人的后代犯了“抄家灭族”之罪,冼氏家族逃到海南这座孤岛上避难。另一说法,俚人有系统有组织地移入海南,始于7世纪初而盛于8世纪,最大规模的迁徙应在冯盎(冼夫人的孙辈)南征之时。在当时,冯冼氏家庭的势力在海南可称“南天一柱”,除了海南岛东北部外,几乎席卷岛上的环海地带。至于哪一种说法最具有权威性,那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不过,老家电白一带的地方方言,讲“黎话”的人居多数,与海南的“黎话”同属一个语系,“黎话”的源头,应在今时的电城山兜丁村,最起码海南及粤西地区一带的“黎话”,是从冼夫人故里丁村传播出去的。有专家推论:电白是俚人望族冼夫人的故乡,海南省的临高、儋州等地的土著多为粤西迁来的俚人,今日称山岭为黎的土著应是古代俚人的后代。
“俚人”,即东汉至五代时生存在粤西、桂东、桂南及越南北部等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先民是先秦时的西瓯、骆越人及汉代的乌浒、南越人。宋代出现的壮人和黎人,是俚人的后裔。冼氏家族“世为南越首领”,而冼夫人又是冼氏家族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由此推论,今天的海南“黎人”,与冼氏家族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小小的丁村,就像一位历史老人,枯坐在那片古老的厚土之上。冬春之交的晌午,落在荒草地上的阳光,是那么的洁白和静穆。
(来源:南方日报)
中华寻根网:http://www.chineseroots.net/news/home/home_lv/20041007/7104475.html
作者:张慧谋
老家在小城南郊。城北十里外的山兜丁村,便是岭南“圣母”冼氏墓的所在地和冼夫人故里。
外人一直以为,山兜丁村同属一处,其实这是误解。冼氏“墓城”遗址在电白山兜,与之相隔三四里地的丁村,才是冼夫人故里。自古以来,山兜丁村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故被人混为一谈。
甲申年农历正月廿五父亲忌日,我回了一趟故乡,顺便去了山兜丁村。村中几位长者,老早就在娘娘庙里等着我们。
看上去,娘娘庙虽然有些破败,但仍遗风犹存,古朴而庄重,不像一些新修的庙宇,大红大绿的俗气得很。娘娘庙后豁出一大片空地,约有五六十亩,茂草疏林,隋代瓦砾俯拾皆是,据说这里就是“隋谯国夫人冼氏墓”遗址。背驮墓碑的那块“?”(龟趺石),像一只千年老龟,闭目静卧,石质坚硬,乌黑发光,至今仍存于“墓城”内,即娘娘庙后。经专家鉴定“龟趺石”为隋物。有趣的是,五六十年代,此石一直遗弃路边,被上山砍柴的樵夫当“磨刀石”,石面的乌亮处,便是磨砍柴刀时留下的痕迹,也是无知和愚昧的反照。
村中长者说,娘娘庙原本是丁村冼氏的宗祠,为纪念先人冼夫人所建。如此说来,娘娘庙应是最早建的冼夫人庙了。建庙年代不详,一种说法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年),却有专家认为,这说法未必确切,况且志书上也没有记载。但今存于娘娘庙里的那只“虎头纹”香炉,属隋物无疑,这倒是实实在在的。
据道光《广东通志》记载:“高州电白县隋谯国夫人冼氏墓在电白县境。县北山兜娘娘庙后有冼夫人墓,去城十里,遗址犹存,碑失。嘉庆二十四知县特克星阿重立碑。”也就是说,我们现时所见的立在“墓城”遗址相思林中的那块墓碑,是后来知县特克星阿重立的,原碑已失。特克星阿从北方来电白做官,想不到他此举却为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寻的历史见证,至少可知隋“隋谯国夫人冼氏墓”的大体方位。
提及冼氏墓,村中的几位老人话语滔滔,他们似乎都有着满肚子说不完的故事。岁数最大的一位,已年过八旬,但老人的记性相当好。他说他小时候,不敢靠近“墓城”半步,偶尔经过这里,也是远远的、怯怯的看上一眼,就赶紧离开。那时的“墓城”有城墙、城河和城池,城墙高过人,城内阴森森的,据说里面还有守墓士兵居住的“兵房”遗址。照此说来,冼氏墓的面积不仅大,其规格也是相当高的。我从一篇研究冼夫人文化的论文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冼夫人的爵位“从其夫”(即隋谯国公冯宝),也即是三品官衔以上,死事也是按此置办。冼夫人本身也受隋帝册封:宋康郡夫人、谯国夫人。并被授权:开幕户、置长史、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官行事。死后又谥为诚敬夫人。在当时,冼夫人的权力不仅是“听发部落六州兵马”那么简单,而且还拥有“先斩后奏”权。难怪南越王墓博物馆顾问、广东考古界老前辈麦英豪先生断言:“在岭南,除了南越王赵陀,惟有冼夫人这么高的封号才能相配。”
冼氏墓经历了1400多年沧桑,当年的辉煌不再,偌大的“墓城”遗物寥寥,但有些地段的城墙,仍是有迹可寻的。村中老人领着我一边走一边回忆,他们指指点点,这块凸起的地方就是老城墙,泥土夯实的,那边是城河,再远点长着竹子的地方是城池……总之,老人们像在向我打开一本纸质发黄的古书,让我阅读。可我却是茫然复茫然,什么也看不到,除了满地的老瓦片和荒草,我真的难以再看到什么。岁月就是这样的无情,再伟大的人物,与凡夫俗子无异,同样是时间的匆匆过客,顶多是在史册上留下一些苍白的文字,或与他生前有关的一些能引起人们对他们缅怀的史迹的印记,仅此而已。
我在“墓城”内默默地走着,不知哪一脚是现实,哪一脚是虚幻,仿佛我每一脚踏下去,都会惊动这位岭南“圣母”的酣梦,都会踏翻一些隋代的瓦当,甚至稍不小心,脚底还会被一枚陪葬的银器或金钗狠狠地扎一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早些年,就有村民在“墓城”里拾到金钗之类的陪葬物。“墓城”颇大,老人带着我从南转到北,又从东转向西,走着走着,额头就冒出细细的汗珠来。墓园内的相思树几乎是朝着一个方向斜斜地生长。晌午的阳光透过林木间,那些相思树,像在俯视,又像在倾听。四周静极了。
我内心一直在思忖着一个问题,偌大的“墓城”空留在村中央,四周都是村舍,竟然没人在这块“风水宝地”建房屋,甚至农作物也没有,就让它白白地空着这么多年,足足十多个世纪了。我问何故?老人说,这里是“冼太妈”(冼夫人)的地方,是块圣地呀。也许是出于后人对冼夫人的敬仰和崇拜吧,他们才会如此自觉地、默默地将“墓城”保护起来。老村长对我说了一件事。80年代初,有邻县人开着一辆汽车来山兜,想搬走那块“龟趺石”,被他和村民阻止了。不久,又有外地人想以六、七万元高价把“龟趺石”买走,同样被村民拒绝。由此可见,这里的村民对冼夫人文物的爱惜和保护意识,是与生俱来的。
我提出要到丁村去走走。丁村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舍零散,几乎建在田地边。这里的田园没有庄稼,显得空旷而恬静。村边东头,有一座小山包,叫丁村岭仔,是隋朝留下的印记。1400多年前,冼夫人的故居就在这里,当地文物部门还在山脚下立了一块碑石:冼夫人故居遗址。
我一个人爬上山头,山顶平坦,有半个足球场大,据说这里是冼夫人习武之地。站在山顶眺望远处,周围都是一马平川的田野。北边的那座高山,是冼氏家族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据说山中还有三只“俚人洞”,洞的直径约3米左右,深度却无人知晓,因为从来没谁有胆量到洞中探个究竟。这三只神秘的洞穴,也是隋代遗留下来的,按专家的说法,“俚人洞”是俚族人躲避外来入侵者的地方。丁村的西南面还有一座小山包,当地人称这里叫“马场”,大概是马房或牧马之地。村边有一片约20余亩的农田,叫“妈田”。俚语“妈”即汉语“婆婆”的意思。“妈田”即冼夫人名份下的田地。冼夫人故居遗址,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草丛里偶尔露出一些厚厚的瓦片,这些不显眼的隋代瓦片已有1400多年历史。要不是阅读碑上的文字,谁会想得到,这地方曾出过一个权力可与南越王赵陀匹故、受到三朝皇帝册封的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今天的丁村村民没有一个是冼姓的后代,都是黄氏家族。何故?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隋唐之交,冼氏家庭倾巢迁徙海南,搬迁的原因有不同版本,一说法是冼夫人的后代犯了“抄家灭族”之罪,冼氏家族逃到海南这座孤岛上避难。另一说法,俚人有系统有组织地移入海南,始于7世纪初而盛于8世纪,最大规模的迁徙应在冯盎(冼夫人的孙辈)南征之时。在当时,冯冼氏家庭的势力在海南可称“南天一柱”,除了海南岛东北部外,几乎席卷岛上的环海地带。至于哪一种说法最具有权威性,那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不过,老家电白一带的地方方言,讲“黎话”的人居多数,与海南的“黎话”同属一个语系,“黎话”的源头,应在今时的电城山兜丁村,最起码海南及粤西地区一带的“黎话”,是从冼夫人故里丁村传播出去的。有专家推论:电白是俚人望族冼夫人的故乡,海南省的临高、儋州等地的土著多为粤西迁来的俚人,今日称山岭为黎的土著应是古代俚人的后代。
“俚人”,即东汉至五代时生存在粤西、桂东、桂南及越南北部等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先民是先秦时的西瓯、骆越人及汉代的乌浒、南越人。宋代出现的壮人和黎人,是俚人的后裔。冼氏家族“世为南越首领”,而冼夫人又是冼氏家族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由此推论,今天的海南“黎人”,与冼氏家族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小小的丁村,就像一位历史老人,枯坐在那片古老的厚土之上。冬春之交的晌午,落在荒草地上的阳光,是那么的洁白和静穆。
(来源:南方日报)
中华寻根网:http://www.chineseroots.net/news/home/home_lv/20041007/7104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