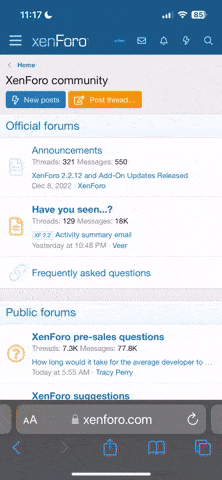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 注册
- 2004-11-13
- 帖子
- 13,391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61
- 年龄
- 38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宣桦一直不肯来道歉,只是发短信给我,“你干吗呢?快回来。”
我不理他。
第四天接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还生气啊?”
不够严肃,我还是置之不理。
在冷战了一星期之后,宣桦终于承认了错误,但是态度还很不严肃,挤牙膏一样敷衍了事,一看就是想蒙混过关的意思。
“什么态度?写检讨!”我嗓子有点儿哑,都是上次哭坏了。
“对,写检讨!”阿雅声援我,“我们陈默可是美女作家,写不深刻了甭想过关。”
“我怎么觉得你骂我呢?去去哪儿凉快哪儿站着去!”我回头对阿雅说,再转过头来,“你不许笑!写你的检讨去!”
“检讨。”宣桦伸出手,信纸中间夹张照片,我抽出来,上面是我和他在山顶拍的照片,我站在宣桦背后掐他脖子,他很配合地把舌头吐得老长,两人脸上都是笑嘻嘻的。
“那天你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宣桦面无表情地看着天花板说,“后来我又自己买了一只挂山上了。默默,我不是不珍惜……”
我闷着头不说话,他轻轻抚摸我的头发,“你说你也不是个小孩儿了……”
我哇地哭出来。
后来宣桦变魔术一样拿出个袋子来,“这个,给你的。”
包得挺严,我接过来打开重重包裹一看,脸立刻红成猴屁股―――是那天我在“爱慕”专柜试的那套内衣。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我蚊子哼哼一样地问他。
“问赵雅的。”宣桦笑得邪邪的,“这个颜色很衬你肤色。”
我忽然想起来什么,“你不说什么都没看见吗?”
……
“老婆饶命。”宣桦站在屋外面拉着房门笑,“我本来是准备夸你身材好的。”
“流氓!”我恨恨地骂,“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人一般色!”一边骂一边打量着衣服。吵一架就给送一套爱慕……那,我还看上套黛安芬呢……什么时候再找碴吵一架?我胡思乱想。
“少在我眼皮底下―――打情骂俏的,”阿雅端着碗粥闲闲地走过来,“自己屋里丢人还丢不够?我都替你俩不好意思。”
宣桦面红耳赤,赶快进了屋儿,我俩对着眼看了半天,宣桦傻笑,我别过脸。
“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宣桦说。
我认认真真点了点头。
在寒假到来之前,还有一场象征意义的考试,我差点忘了。
人到大三,激情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只有班头儿和吕小倩之流还在拼命刷青漆装嫩在老师和新生面前蹦Q(阿雅话说“伪高潮”),那也是职业需要,谁愿意看下属一副萎靡不振的德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都不容易。
逃了有快俩月的课,重回教室看见老师都有点眼生,其实我上自习上烦了,偶尔也会来上节把课,坐最后一排做英语仿真试题,小山一样的卷子层出不穷,做也做不完,就好像高考那时候天天做大卷子,做完黄冈的做海淀的,做完海淀的做苏州的。做到六亲不认就认得卷子。宣桦那个畜牲还经常看着卷子上的涂改痕迹鄙视我,我问他题,要是有点难度的还好,要是题弱智点或是我粗心大意犯了不该犯的错,他非但不给讲还极其鄙夷地说“Banana”,可不是香蕉,是骂我“傻瓜”。我属于情绪型的选手,热情被人一打击,越发接二连三地出错误,宣桦看着我的卷子,从头到尾至少说了十个“Banana”。我都快成盛产香蕉的洪都拉斯了,一怒之下我把卷子带进课堂,再也不让他看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
同学们也有一阵子没见了,大家凑一起唠嗑重新熟悉,“你这两天在哪儿呢?”“三教啊。”“嘿!我也天天三教怎么没看见你呢?”“你除了美眉还看得见别人么?”
老师一声咳嗽,“上课。”
老师习惯给十几二十几个人上课了,骤然看见坐得满满的课堂还露出一点骇然之色,当下受宠若惊地拖过花名册,“同学们下课后来签到。在课堂上发过言参与过讨论的同学也写个名字条儿交上来,平时成绩可以加分。”
宣桦一直不肯来道歉,只是发短信给我,“你干吗呢?快回来。”
我不理他。
第四天接到了他的电子邮件,“还生气啊?”
不够严肃,我还是置之不理。
在冷战了一星期之后,宣桦终于承认了错误,但是态度还很不严肃,挤牙膏一样敷衍了事,一看就是想蒙混过关的意思。
“什么态度?写检讨!”我嗓子有点儿哑,都是上次哭坏了。
“对,写检讨!”阿雅声援我,“我们陈默可是美女作家,写不深刻了甭想过关。”
“我怎么觉得你骂我呢?去去哪儿凉快哪儿站着去!”我回头对阿雅说,再转过头来,“你不许笑!写你的检讨去!”
“检讨。”宣桦伸出手,信纸中间夹张照片,我抽出来,上面是我和他在山顶拍的照片,我站在宣桦背后掐他脖子,他很配合地把舌头吐得老长,两人脸上都是笑嘻嘻的。
“那天你一走我就后悔了,真的。”宣桦面无表情地看着天花板说,“后来我又自己买了一只挂山上了。默默,我不是不珍惜……”
我闷着头不说话,他轻轻抚摸我的头发,“你说你也不是个小孩儿了……”
我哇地哭出来。
后来宣桦变魔术一样拿出个袋子来,“这个,给你的。”
包得挺严,我接过来打开重重包裹一看,脸立刻红成猴屁股―――是那天我在“爱慕”专柜试的那套内衣。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我蚊子哼哼一样地问他。
“问赵雅的。”宣桦笑得邪邪的,“这个颜色很衬你肤色。”
我忽然想起来什么,“你不说什么都没看见吗?”
……
“老婆饶命。”宣桦站在屋外面拉着房门笑,“我本来是准备夸你身材好的。”
“流氓!”我恨恨地骂,“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男人一般色!”一边骂一边打量着衣服。吵一架就给送一套爱慕……那,我还看上套黛安芬呢……什么时候再找碴吵一架?我胡思乱想。
“少在我眼皮底下―――打情骂俏的,”阿雅端着碗粥闲闲地走过来,“自己屋里丢人还丢不够?我都替你俩不好意思。”
宣桦面红耳赤,赶快进了屋儿,我俩对着眼看了半天,宣桦傻笑,我别过脸。
“以后再也不要吵架了。”宣桦说。
我认认真真点了点头。
在寒假到来之前,还有一场象征意义的考试,我差点忘了。
人到大三,激情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只有班头儿和吕小倩之流还在拼命刷青漆装嫩在老师和新生面前蹦Q(阿雅话说“伪高潮”),那也是职业需要,谁愿意看下属一副萎靡不振的德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都不容易。
逃了有快俩月的课,重回教室看见老师都有点眼生,其实我上自习上烦了,偶尔也会来上节把课,坐最后一排做英语仿真试题,小山一样的卷子层出不穷,做也做不完,就好像高考那时候天天做大卷子,做完黄冈的做海淀的,做完海淀的做苏州的。做到六亲不认就认得卷子。宣桦那个畜牲还经常看着卷子上的涂改痕迹鄙视我,我问他题,要是有点难度的还好,要是题弱智点或是我粗心大意犯了不该犯的错,他非但不给讲还极其鄙夷地说“Banana”,可不是香蕉,是骂我“傻瓜”。我属于情绪型的选手,热情被人一打击,越发接二连三地出错误,宣桦看着我的卷子,从头到尾至少说了十个“Banana”。我都快成盛产香蕉的洪都拉斯了,一怒之下我把卷子带进课堂,再也不让他看了,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
同学们也有一阵子没见了,大家凑一起唠嗑重新熟悉,“你这两天在哪儿呢?”“三教啊。”“嘿!我也天天三教怎么没看见你呢?”“你除了美眉还看得见别人么?”
老师一声咳嗽,“上课。”
老师习惯给十几二十几个人上课了,骤然看见坐得满满的课堂还露出一点骇然之色,当下受宠若惊地拖过花名册,“同学们下课后来签到。在课堂上发过言参与过讨论的同学也写个名字条儿交上来,平时成绩可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