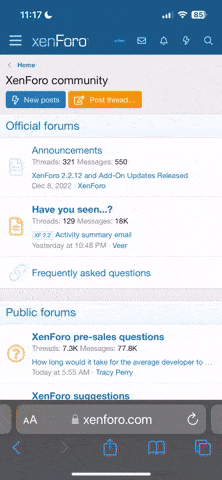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五四”纪念碑 (2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azhong339
- 开始时间
azhong339
初中三年级
- 注册
- 2006-05-14
- 帖子
- 526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0
- 年龄
- 63
[转载]: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504/n263755715.shtml
《五四: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2009年05月04日08:32
来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米德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 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努力。
时代周报:通常我们认为自清朝末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可以说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问“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妇女问题、内战问题?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吗?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等等。
“五四”探索中国各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中国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我很感兴趣你的“塑造”(shape)的说法,你认为现代中国的哪些方面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
米德:我的确是说“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很重要,可是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五四”以外的影响不重要,现代中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思想、孔子思想,还有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我来说,1919年前后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氛围营造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塑造了此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这个现象被称为“五四”。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出现的说法。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创造了一段传奇,在此后的年代它成为了一个标签,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现在,“五四”提出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每隔一个20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就中国的资源展开争夺;40年代,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千万中国人死在战场;60年代,走出战争梦魇并迎来共产主义胜利的中国,发现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时代周报:相比90年前,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认为中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强大,为什么你认为现在中国还要问和90年前一样的问题?
米德:当然,现在的中国很强大,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很弱小,现在的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我想,中国和欧盟在很多方面相似,它们都是很强的经济体,有很强的国际影响,但是欧盟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还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够清楚。
时代周报:你反复强调“五四”问出了关键性的中国问题,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可能也会告诉你,“五四”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米德:“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指出了一条道路,而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展开了探索,为当时的中国摆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是走入了误区。
时代周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最经典的词汇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思想,或者说是救国道路,这两个词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普遍适用,“科学”和“民主”两个词有时甚至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想都不用多想就可以脱口而出。而在当时,“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如何提出来的?你认为它和今天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民主、科学是一个意思吗?
米德:我想这里要区分当时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南非是完全的殖民地,都有独立的愿望,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但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办法,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印度采用的是“宗教”,虽然印度独立运动不是一场“宗教”运动,甘地本人也没有宗教偏见,但是他对宗教的问题感兴趣,他以宗教认同方式发动独立运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没有这个机会,中国当时虽然也有各种宗教存在,但是在“救国”的问题上,宗教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而在南非,“种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南非的独立运动从区分黑人和白人入手,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中国“五四”时期的救国方式,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两点生动反映的,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提出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组合,是一个中国创造。如果你看看别的国家,比如印度,我想他们的甘地对“民主”可能感兴趣,但是对“科学”他真的不感冒,他甚至发动国货运动,提倡印度人自力更生,这可能与印度在当时没有发生内部的战争有关,而中国同时碰到了内部和外部战争,每当战争发生,人们就重视起科学技术的问题来。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说起“五四”,耳熟能详的主题还有“破除礼教”、“全盘西化”等,但是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的书里却认为这些都是被误读了的“五四”,你认为这些说法问题在哪里?
米德:在反对儒家传统的问题上,也许中国人通常的说法是,五四启蒙运动发动中国人反抗落后的、压迫的、家长式的儒家文化。但其实这个不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最为激进的五四参与者是彻底反对儒家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改良中国传统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正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是越战胜利的美国,同时也是反越战游行深入人心的美国一样,“五四”也不能仅仅总结为所谓的“进步”力量胜过“保守”力量,至少在思想领域,当时同时并存着各种思潮。
关于西化的问题,“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倾慕所谓的“西方”,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并不热衷于“西化”,即使是“五四”中最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的人。而且,中国人感兴趣的欧洲世界,常常不是最强大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而是新近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比如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些国家做到了当时的中国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的思想家希望借鉴它们的经验。
时代周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在批判地思考“五四”影响,如果说在过去对“五四”持高度肯定的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又有走向过度否定的危险,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五四”开出的“恶之花”,当下中国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五四”激进主义带来的,你认为这是理性的态度吗?
米德:批评“五四”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这个声音一直存在,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就曾说“五四”引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是一种污染。但是我想说的是,“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每次我听到当下的中国学者批评“五四”,我认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需要取“五四”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批评,这就像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时候取“五四”的某一些方面进行弘扬。比如,“五四”有一个方面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有一些人就借“五四”的这个方面来号召大众“批孔”,认为反对儒家是“五四精神”,但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一种思想,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不是全部。所以我想,他们批评的是他们想要批评的,因为“五四”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时代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说“五四”更多的是一个会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处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而不仅仅是某一样东西?
米德:“五四”的力量不在于某一条道路、某一个思想,而是思想、道路的百花齐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五四”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对中国道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探索。
来源:时代周报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504/n263755715.shtml
《五四: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2009年05月04日08:32
来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米德
海外汉学方兴未艾,英国的汉学家也不在少数,但是要找到一个专事“五四运动”研究的汉学家并不容易。与多位英国的汉学家数次邮件往返,却屡屡被告知“此非专长,恕难相告”。之后,记者转向了图书馆,搜寻中,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出现在“中国相关”书架上,名曰《痛苦的革命: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正是探讨五四运动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政治。而令人兴奋的是,其作者拉纳。米德教授所在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与记者所在的牛津大学路透传媒研究所,巧合地同属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
又一个星期的邮件等待之后,复活节前夕(4月10日),刚刚从日本搜集中日战争资料返回英国的米德教授,在他牛津的家中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窗外春雨迷蒙,沙发上的防尘罩还没来得及拿掉,米德时而英文时而中文,显露出与他的年龄不甚相称的睿智。
米德1969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小郡苏塞克斯(Sussex)长大,他从小就对中国话题感兴趣,后来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移居牛津,从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政治。他的学术研究,试图从战争和侵略之中,找到它们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联系,其中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200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痛苦的革命》。该书围绕“五四”,讲述中国在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走向现代国家道路上经历的一系列痛苦不堪、至今尚难说完成的斗争。次年,米德因为该书获得英国学术著作奖,并被评为2005年度英国青年学者。
米德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不在于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影响了此后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也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 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同时,“五四”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它问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
“五四”提出“中国怎么办?”
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
时代周报:你用“bitter”来形容“五四”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翻译为中文,它是“痛苦”、“苦涩”的意思,实际上,鲁迅就曾经说过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选择这个词的用意是什么呢?
米德:我用“bitter”这个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时候,经历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加艰难的时期。我主要指的是里面的“冲突”。从前半期的抗日战争、内战,到后半期的“文革”等,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冲突的历史,这种冲突充满着你死我活的争夺。而因为世界大战的发生,这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
同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冲突的政治,那时的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有一个“民主”的系统。在那个系统内,人们反对这个或者那个政党,但是不反对“民主”系统,而中国那个时候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但是它们不能在一个系统里同时存在,两个党只有一个党可以存在,所以,这个政治也完全是一个冲突的政治。20世纪的中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两个事件,都是非常激烈的“冲突”。一个是抗日战争,中国人反对日本人入侵,这是真枪实弹的冲突;另一个是共和国期间的政治。这些经历,足以形容为“痛苦”。
时代周报:那么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
米德:“五四”运动对中国的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不在于一群学生走上街头烧了一个赵家楼,而在于它所孕育的社会氛围和政治情绪。“五四”并非因为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而重要,而是串起了一个时代(a time)、一种氛围(anatmosphere)、一种情绪(a mood) 和一种影响今日中国社会、政治的能量(an energy)。
虽然中国从20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变化之中的不变是自“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在问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的政治先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世界,中国应该怎么办?我认为这个问题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我想民国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在问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国还要问这个问题。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国经历了“痛苦”的战争和冲突。而“五四”的重要性,就在于它问出了这个承前启后的问题,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可以看作是中国人为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或者说努力。
时代周报:通常我们认为自清朝末期中国遭到列强侵略以来,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救国”运动,可以说早在1919年之前就开始问“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为什么你认为“五四”才是最重要的呢?
米德:中国的确有很多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1898年清末的“戊戌变法”,但是“五四”时期人们问出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如何解决贫困问题、妇女问题、内战问题?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国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吗?中国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等等。
“五四”探索中国各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中国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我很感兴趣你的“塑造”(shape)的说法,你认为现代中国的哪些方面是被“五四”塑造出来的?
米德:我的确是说“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很重要,可是这里要小心一点,我不是说“五四”以外的影响不重要,现代中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毛泽东思想、孔子思想,还有类似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记忆。但是对我来说,1919年前后的政治情绪和社会氛围营造出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塑造了此后整个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这个现象被称为“五四”。对政治、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中国人,他们用的语言,他们用的思想,大多数用的还是“五四”出现的说法。
“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创造了一段传奇,在此后的年代它成为了一个标签,不同的政治组织都试图从“五四”一系列的事件或者思想流派中寻找为其所用的因素。此外,直到现在,“五四”提出的问题还在困扰着中国。
20世纪的中国,每隔一个20年都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20年代,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同时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就中国的资源展开争夺;40年代,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千万中国人死在战场;60年代,走出战争梦魇并迎来共产主义胜利的中国,发现自己又陷入“文化大革命”之中。
时代周报:相比90年前,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认为中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强大,为什么你认为现在中国还要问和90年前一样的问题?
米德:当然,现在的中国很强大,而“五四”时期的中国很弱小,现在的中国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但是我想,中国和欧盟在很多方面相似,它们都是很强的经济体,有很强的国际影响,但是欧盟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还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够清楚。
时代周报:你反复强调“五四”问出了关键性的中国问题,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可能也会告诉你,“五四”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米德:“五四”的意义不在于指出了一条道路,而是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可能性展开了探索,为当时的中国摆出了各种不同的选择。“五四”时期各种政治思潮非常复杂,但这种复杂正是最大范围地反映了中国所具有的五彩纷呈、激动人心的可能性。
90年后的中国仍在寻找答案
“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是走入了误区。
时代周报:“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最经典的词汇之一,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思想,或者说是救国道路,这两个词在9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普遍适用,“科学”和“民主”两个词有时甚至如此自然,以至于人们想都不用多想就可以脱口而出。而在当时,“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如何提出来的?你认为它和今天我们挂在口头上的民主、科学是一个意思吗?
米德:我想这里要区分当时中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那时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南非是完全的殖民地,都有独立的愿望,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诉求,但是它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办法,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印度采用的是“宗教”,虽然印度独立运动不是一场“宗教”运动,甘地本人也没有宗教偏见,但是他对宗教的问题感兴趣,他以宗教认同方式发动独立运动,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中国没有这个机会,中国当时虽然也有各种宗教存在,但是在“救国”的问题上,宗教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而在南非,“种族”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南非的独立运动从区分黑人和白人入手,而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是不存在的。
中国“五四”时期的救国方式,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科学技术的革新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两点生动反映的,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把“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提出来,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组合,是一个中国创造。如果你看看别的国家,比如印度,我想他们的甘地对“民主”可能感兴趣,但是对“科学”他真的不感冒,他甚至发动国货运动,提倡印度人自力更生,这可能与印度在当时没有发生内部的战争有关,而中国同时碰到了内部和外部战争,每当战争发生,人们就重视起科学技术的问题来。
时代周报:我们中国人说起“五四”,耳熟能详的主题还有“破除礼教”、“全盘西化”等,但是我感到吃惊的是,你的书里却认为这些都是被误读了的“五四”,你认为这些说法问题在哪里?
米德:在反对儒家传统的问题上,也许中国人通常的说法是,五四启蒙运动发动中国人反抗落后的、压迫的、家长式的儒家文化。但其实这个不是事实,实际上只有少数几个最为激进的五四参与者是彻底反对儒家的,而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改良中国传统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正像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不仅是越战胜利的美国,同时也是反越战游行深入人心的美国一样,“五四”也不能仅仅总结为所谓的“进步”力量胜过“保守”力量,至少在思想领域,当时同时并存着各种思潮。
关于西化的问题,“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倾慕所谓的“西方”,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并不热衷于“西化”,即使是“五四”中最激烈地反对中国传统的人。而且,中国人感兴趣的欧洲世界,常常不是最强大的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而是新近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比如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些国家做到了当时的中国想做而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的思想家希望借鉴它们的经验。
时代周报:这些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开始在批判地思考“五四”影响,如果说在过去对“五四”持高度肯定的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似乎又有走向过度否定的危险,有学者甚至认为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是“五四”开出的“恶之花”,当下中国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五四”激进主义带来的,你认为这是理性的态度吗?
米德:批评“五四”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这个声音一直存在,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就曾说“五四”引进的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是一种污染。但是我想说的是,“五四”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不是一元的,而是包含着多元化的政见、思潮和辩论。一概而论“五四精神”就走入了误区。所以每次我听到当下的中国学者批评“五四”,我认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根据自己的需要取“五四”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批评,这就像另外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时候取“五四”的某一些方面进行弘扬。比如,“五四”有一个方面是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上世纪60年代的“文革”期间,有一些人就借“五四”的这个方面来号召大众“批孔”,认为反对儒家是“五四精神”,但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一种思想,一部分人的观点,而不是全部。所以我想,他们批评的是他们想要批评的,因为“五四”有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
时代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说“五四”更多的是一个会诊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处方,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容器而不仅仅是某一样东西?
米德:“五四”的力量不在于某一条道路、某一个思想,而是思想、道路的百花齐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五四”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什么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对中国道路的各种可能性展开探索。
来源:时代周报
相似主题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3 (会员: 0, 游客: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