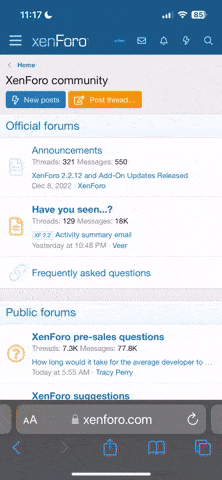小时候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语言是那样的孤单。出门在外很多年了,从离开家乡的那个镇算起,我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找到共同语言。不是不能交流,而是找不到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口音的人,我只能说着茂名话夹杂着广州话的方言,抑或是电白的闽方言俚话。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在茂名幸福路的一间快餐店吃饭,听到旁边的两位先生在用我熟悉的家乡话肆无忌惮地高谈阔论,我顿时喜出望外,赶忙过去套近乎,原来他们是大衙人。此后在外,熟悉的乡音不再耳闻。
从来没有语言学者对我的家乡话研究定性过,我只好自己把它定义为“七迳白话”。七迳白话,可以断定是粤方言,从大的范围来说,属于学者们划分的粤方言中的高阳方言片的地域范畴。但是从语调和词汇上来说,它又不属于以地域划分的“茂名话”(又名“高州话”),甚至可能不属于高阳方言片这个宽泛的学术范畴。
目前操这种粤方言的地域,全省只有七迳、大衙(已合并到林头镇)两个镇的一部分地方,而且这两个镇相互毗邻,都是客家、福佬、广府三大民系杂居的地方,可想而知,它的范围是多么有限和孤单。这个地域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方言孤岛。然而更大的方言孤岛在包围着这个小孤岛。囿于电白这个几乎纯粹的闽方言的环境,在闽方言(当地人称之为“俚话”)的孤岛中,七迳白话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并不是指它的发音受到了闽语的影响,而是在词汇上大量吸收了闽语词汇。七迳白话有两到三成左右的词汇能在俚话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家乡人称自己的方言为“白话”,说俚话的人则把这种白话称之为“客话”,称“讲白”为“讲客”。这个客话,不是客家话的意思,而是福佬民系为主人,我们这个民系(属广府民系)为客人的意思,这反映了在古时候的电白县,福佬人先入为主,先祖们后入为客的事实,三大民系共同开发了电白。
因为民系的融合,家乡人日常生活中往往双语并用,以白话为主,俚话亦相当熟练。这是语言和民系融合的十分典型的实证,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个十分有学术价值的事实。电白的方言众多,俚话(以霞洞为代表),客家话(以沙琅为代表),海话、军话、旧时正话(以电城为代表),蛋家话(以博贺为代表)都有语言学者做了研究,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唯独七迳白话,至今还没有人做研究。对于它的形成、归属划分和特点,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想,这也是因为家乡话范围过小所致,在地域上仅仅相当于一个镇的面积。而且说这种话的人数太少,目前不足8万人。相对本地其它方言而言,实在微不足道,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无庸置疑,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和十分珍贵的语言融合的实证,甚至可以称为濒危方言,这种方言研究的空白十分值得去研究。
我很想去做这项工作,但是我没有语言天赋,况且语言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现在普通话的教学已经日渐影响到方言的词汇,家乡很多地道的方言年轻一代逐渐在摒弃。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多词汇只会用普通话拼读,却不能用粤语读出来。回顾以往,很多小时候会说的方言词汇,现在都已经退化,口语正在让位于书面语,可以说家乡方言词汇流失的现象不可避免。
既然无法对家乡话做考证,只好罗列出一些十分特别的口语词汇,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下面列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口语词汇,至于与其他粤方言说法相同的词汇,一般不作列举。以下所举的例子,也许你都能看得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仔细想想,在日常生活中你却可能不会那样子说,而是别的说法,其实这就我和你的区别。
香与臭系列――家乡话“香”“臭”不分,有如茂名话“买”“卖”不分。乡亲们闻到某种气味,可以说“香某种味道”,也可以说“臭某种味道”,但这是有限度的,中性气味的东西可以“香”“臭”不区分,但真正污秽臭味的气味只能用臭。这也是家乡话中非常特色的地方。茂名话“买”“卖”不分是没有限度的,无论是“买”还是“卖”,都只说“卖”,假设茂名人对你说“卖了某东西”,如果不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你是不知道他是“买”还是“卖”的。呵呵,扯远了,但从这里就知道家乡话与茂名话不是同一路的。
刀系列――“小刀”称为“刀仔”,“菜刀”称为“薄刀”,“大刀、砍刀、柴刀”称为“刀p”。我把这些说法与室友交流的时候,他们笑得肚子直叫痛,因为他们无法明白,这“刀”分出大小和种类犹自可,但是又如何分出性别的?如何会有公和母(p)的区别?虽然很好笑,但我无法解释。
数量系列――“几十万疃唷保不是真的是数量“几十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很多,这是家乡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溜溜”在家乡话中是个很有意思的量词,意思是说“很多很多”,比方说以前家乡经常说但现在很多人遗忘了的――“嗯,人溜溜,贼溜溜,鬼溜溜”,就是说“人很多,贼很多,鬼也很多。”呵呵,很搞笑。
地理系列――称小河为“圳仔”。深圳的大名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深圳”这个词没几个人真的懂得。“深圳”的本意是指什么?要是你问我家乡人,他们会告诉你,所谓“深圳”,就是一条深深的河流。深圳的得名,其实源于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河”。“山窿”――茂密的树林。“田基”――田中小路。称“中间”为“dōng间头”。
时间与做饭系列:
朝早头――清晨,早上。广州话为“早晨”。“晏咒头”――晌午,下午。“晏咒过”――时间过了下午,或者表示迟到得厉害。“麻\头”――实应作“晚黑头”,夜晚,晚上。 “做到晒黑”――不是干活干到被太阳晒黑的意思,而是干活干到天都黑了的意思,“晒黑”就是“夜晚”。
做饭是“煮朝,煮晏,煮晚,煮汤”,当然也可以用“煲粥,煲饭,煲汤”来代替。食朝――吃早餐,食晏――吃午餐,食晚――吃晚餐。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夕阳晚照在村头的池塘上,妈妈的呼唤远远传来――“快番屋几(企)食晚啊。(快回家吃晚饭)”,温情得很。
出门问候三句话系列――身为家乡人,如果不会这三句话,你不应该出门的。
第一句,“食啊嘛?”――意为“你吃了吗?”。这是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只要碰到隔离邻舍,每见一次,必然要说一次。
第二句,“做乜工啊?”。做工――干活,上班。“做乜工啊?(你去做什么工作?你去干什么活?)”同为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基本要说一次,出门干农活或者在路上见面必然要说一次。
第三句,“去书腻”――去哪里。这个词汇只是音译,正式词汇如何写,还不知道。广州话说“去边道”,茂名话说“去书试”。“去书腻啊?”为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几乎要说一次。
儿女教育五句话系列――似乎是家乡人建立的儿女教育的体系。
第一句,“知头知路”――主动,醒目,知道情况。不用别人出声,自己也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这是家乡父母教育儿女应该怎样做事的必备词汇。
第二句,“执头执尾”――收拾屋里零碎的东西。这也是家乡父母教育儿女应该勤快做家务的必备词汇,主要适用于女孩,早晨起床必备功课,呵呵。
第三句,“夹手夹脚,郁手郁脚”。“夹手夹脚”是教育孩子要有团队合作精神,是“齐心协力,一起动手”的意思。“郁手郁脚” ――不是广州话里的做出一些侵犯别人的不礼貌的动作的意思,而是自己动手去做去帮忙的意思,教育孩子不要懒惰,凡事要自己去做。
第四句,“画公仔画出肠”――话说得太明白,或做事多此一举。父母会经常教导你“毋(母)画公仔画出肠”,意为说话做事应该含蓄点,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第五句,“督人背脊”――打别人的小报告,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父母会经常提醒你“毋(母)督人背脊”(不要在背后说人长短),既是处事方式,又是品德要求。
骂人四句话系列:
第一句,“车大炮”――假话,吹牛,也可引申为侃侃而谈。家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据说广州话也有这个说法,但也只有老广州才能明白。现在的广州话里基本用“吹水”来代替了它的位置。其实“车大炮”是很有渊源的。一些说法是认为来源于古文字或者是象棋。我觉得不然。我认为这个词是近代才出现的。孙中山闹革命之初,无车又无炮,革命成败没有保障,孙中山对民众的承诺也是一句空话,他的政治对手讥笑他在吹牛,所以人称“孙大炮”。家乡人又说“大炮王”,意为满口都是谎话假话的人。
第二句,“断你种、短你命”――原意是一种十分恶毒的骂人的话,诅咒别人短命和没有后代。但在家乡,实际上,仅仅含有责备的意思,连父母都经常这样骂自己的孩子。别人听来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第三句,“粪箕秧、火秧”――同样是咒骂小孩的话,相传以前小孩夭折了就用粪箕装好拿去埋,所以骂人“粪箕秧”是很狠毒的,是咒人死。但是实际上骂人“粪箕秧”其实不是真的恨到入骨非要咒人死,“粪箕秧”现在只是纯粹一句骂人的话,父母生气了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也会骂粪箕秧。
第四句,“马骝仔、马骝婆、马骝精”――广州话有马骝仔的说法,但我敢说绝对没有马骝婆这种说法。家乡话里马骝仔的意思可以是指调皮的男孩子,也可以是仅仅表示对某个男孩子的不屑。马骝婆就是骂女人的话了,无论是少女还是中年乃至老年妇女,如果人家狠狠说你“马骝婆”,你要注意了。但与你相好的好友戏谑地说你“马骝婆”,只是跟你说笑取乐而已。
特色系列:
毋(母)――“无”,与“有”相对,表否定。这是家乡话较特别的地方,既不说北方话的“不”和“没”,又不说茂名话的“印保ǘ磷鳌懊,máo”),亦不说广州话的“唔”。
壳――勺子。制作勺子的原始材料,应该就是植物的硬壳。茂名话说“勺”。家乡人只要这个讲法一出口,别的地方的人一定是莫名其妙。
箸――筷子。广州话虽然有这个说法,但这样说的广州人不多了,几乎用筷子代替了。
望火――煮饭的时候,看着灶火,不让火熄灭和烧了其他地方或者是掌握好火候。望火是家乡的小孩子必修的课程,年幼的孩子干不了什么,还未能“帮手(帮忙)”,父母就经常叫孩子“得闲(有空)”去“望望火”。
飞头――理发,也作“剪头”。乍听上去像是杀头,似乎是清皇朝高压民族压迫政策的残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讲笑)。其实就算是头发,家乡也只说“头毛”。
颈渴――口渴。有时候也使用“口渴”。俚话称为“喉渴”。口渴的同时也就是喉咙干渴和颈部干渴的同时。真是无奇不有,到底是“颈渴”还是“口渴”还是“喉渴”?我看就算是医学的专业人士也分不清楚。
鸡春――鸡蛋。“春”表“蛋”,鸭春为鸭蛋,以此类推。外地人初次听的时候简直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这几乎是家乡词汇独一无二的地方,凭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家乡话。
做米乙――米乙是米粉做的一种过节用的食品。这一种食品,俚话统称为“buǎ(没有文字表述)”,潮汕地区称为糍粑,茂名话也叫米乙,但发音和家乡话不同。小时候隔离村极少数人甚至有一种说法,不知语出何处,直接叫做“妈”。称做米乙为做妈,感觉一定很怪。
趁嘘――用北方话解释就是“赶集”。广州话说“上街、逛街”,虽然意思相近,但趁嘘不同于上街,上街的主要意思是到街上购物游玩,而趁嘘的主要意思农村人到镇上做买卖。
肚疼――顾名思义,是说肚子疼痛。但这里的主要意思,却不是说肚子疼,“好肚疼凇辈皇恰八疼得厉害”的意思,而是“非常喜欢、疼爱她”的意思,一般用于形容长辈对晚辈的喜爱。
书房――上学,“去书房”意为“去上学”,这是十分文雅而且很形象的说法。俚话也是用这个词汇。出门在外,除了吴川话和化州话,我很少听到这种说法。
作仔――鸟类的统称。实应作“雀仔”,但家乡人发音却为“作仔”,这个讲法茂名话也有,但家乡话的发音,茂名人不晓得。
去哨、去料 ――“去哨”不是去放哨,“去料”也不是工厂里的来料加工,这两个词都是“去玩”的意思。
睇过――在广州话里有“看一看”的意思,在家乡这个说法也有这种意思,但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先等一等,先看一看情况再说”。
生丁―陌生、生疏。这个讲法估计广州人听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茂名人有一部分人能听懂,例如羊角那边。
做屋――盖房子,俚话也有这个词汇。广州话为“起屋、起楼”。这个说法估计听过的人不多。
复餐――表面意思是“加餐”,实际意思却是“夜宵”。只能用于吃完晚饭后的加餐,其余加餐则不能用。
失魂――晕倒,精神恍惚。
抵力――生病或者很难受。生病原本就是很耗力气的事情,故说“抵力”。而有时候想表达很难受的感觉或者很看不惯(广州人说“难顶”)也可以说抵力,比如:我见到冢假设是丑女)就抵力(我见到她就难受)。
灶下――厨房。俚话叫“灶庐”,都几形象的。
火水――煤油。因为使用煤油点灯的人不多了,这个称呼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līn地――撒赖,哭着在地上不停地滚动。小孩子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经常向大人表现出来的动作。
兑命――不是要与人交换性命,而是以撒赖为要挟,以达到目的。小孩子经常向大人“兑命”。
火起――不是发生火灾,而是生气了,又经常说“发火”,也经常说“火滚(恼火)”,甚至于“把几火(一肚子火)”。
够担――形容两个人关系很好,气味相投。香港粤语叫“一担(声调:阴平,名词)担(音调:去声,动词)”。
āo wū ――发音如此,没有文字。这是大人哄三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形容小孩子疼的感觉。
恶教 ――难教育,不听话,说了也不听。
恶刮――态度恶劣。也经常说“恶死”。“恶刮到死”意思是“态度差到极点了”。
多口――口只有一个,是不会多的。“口多多”是指“八卦,说是非”。
浪冻――指让高温的物体温度降下来。
琼干――特指让液体挥发掉或者凝固起来。
捞食――不是“搅拌食物”,而是“谋生”的意思。
索烟――不是向人索要烟,而是抽烟,广州话为“食烟”。
交关――事态严重,同“弊”。广州话不会这样,他们说“大镬”!
银包――钱包,广州话作“荷包”。银纸――钱,钞票。
折秃――做孽,遭遇悲惨。广州话叫折堕。
注意――小心。
混帐――不像话,不同意,反对,乱来的。
嬲气――生气。甚至“嬲爆胆(气冲冲)”。“谷气”――“憋气”。至于“激气”,则是“心里有气”。
特停――故意的。广州话说“专登”。
心水――“心意”。“心息”就要“死心”了。“心抱”却是“媳妇”。 “收心”是要“专心一点,或者是死心了放弃吧”,“心落”是说“放心了”。
huàn大――养大 。
yào hái――只是谐音的音译,没有文字。意思是“抓痒”。
压萨――没有文字,音译,但不是很谐音。意思是“吝啬”,广州话说“孤寒”。家乡也说“孤寒”,除了有这个意思,还有“家境寒苦”的意思。
扫山――不是到山上去打扫清洁,而是去扫墓。
混人――不是出来混的人,而是“欺骗人”。
摞雷――找麻烦 。“雷”其实应做“来”。“自己摞雷”意思是“自己找来的麻烦”。
爱嘛?――要吗?要不要?
例头――里面。“下低头”――“下面”。而俚话说“里面”和“下面”都是说“底头”。
做得――行,可以,表示肯定、同意、承诺。
浪衫――晾衣服 。
日头――太阳 。
屈头――转弯。
好劲、好叻――很厉害。这和茂名话明显不同,茂名人说“好强”。
头壳――脑袋。
假衣车――意为“假装”,装模作样。为什么这样说,我至今不明白。
打白脚――赤着脚,不穿鞋子。小时候我经常打白脚,家人恐吓我说会“大脚板(脚底会变得很大)”。
打白手――两手空空。去“探”(看望)“人家(别人)”,“打白手”是被视为不礼貌的表现。这和上面的“打白脚”字面上好像很相近,其实意思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
细蚊仔――小孩。茂名话叫“细弄”,俚话叫“细弄仔”,广州话叫“细路哥”。
猛去咧――你够胆(有胆量)就去吧!这是家乡的父母恐吓孩子、不让孩子去做某些事情的必备语录。
喊乜人――“你喊乜人啊?”不是对着什么人叫喊的意思,而是“你找谁?”的意思,同时又是“你安排谁?”的意思。
托大脚――拍马屁。现在很多人只会说“擦鞋”了。
打乞超――打喷嚏。
偷盐蛇――不是什么蛇,而是壁虎。因为它经常在厨房盐煲旁边出没,农村人以为它会偷吃盐,其实偷盐蛇不偷盐。
走无尾、搏命走――拼命走。广州人说“走甲唔头”。
捞油水――占便宜,着数。
毋(母)着数――不值得。没有便宜占。
毋(母)著衫――赤着上身。广州话叫“打大赤肋”。
落雨咪――下着毛毛雨。
钱蚕舂(音译)―― 广州话叫“教剪踏 ”,北方话叫“剪刀石头布”。
XX转――晕头转向。
一阵仔――一阵间。
眼崛崛――瞪大眼睛,表示不满或生气。“眼蛇蛇”、“眼够够”则是说“不敢正视,只好斜视着”。
好怕擂擂――态度恶劣得很,使人害怕。
ài交打交――吵架打架。
nòng kiào kiào――全烧焦了。
稀pá lá――稀巴烂。
打百分――打扑克。又叫“打牌”,“打pie”。
收起身――藏起来,整理放好。
茄呢茄liě――古里古怪 。
落水踏帝――下着雨,湿漉漉的。
吟吟寻寻――有时候也说“罗罗嗦嗦”,意为喋喋不休,说过不停。
执人口水――又一说法是“口水王”,有时候也说“学口学舌”。都是同一个意思,意为鹦鹉学舌,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好怕到死――不是“很害怕死”,而是“害怕到要死”,形容装扮很难看,面色很难看,样子很令人害怕(广州话“得人惊”)等等。
以上这些,只是家乡方言词汇的一个断面。当然还有很多经典的词汇,一时之间数之不尽,要做这个整理工作,实在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很多口语,有音无字,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粤方言又几乎出口就是古汉语、古文字、生僻字,就算有字也没能认出几个来,更写不出来,以致很多生动活泼的家乡话没法表述。一种方言最重要的其实是语音,是凭藉着发音来与其他方言相互区别的,而词汇相对来说则显得没语音那么重要。由于个人能力不足,家乡话的语音与其他粤方言的区别和归类只能有待有心人去做,它的起源和演变也有待探究。我对家乡方言词汇的介绍也到此为止,希望大家中意。
从来没有语言学者对我的家乡话研究定性过,我只好自己把它定义为“七迳白话”。七迳白话,可以断定是粤方言,从大的范围来说,属于学者们划分的粤方言中的高阳方言片的地域范畴。但是从语调和词汇上来说,它又不属于以地域划分的“茂名话”(又名“高州话”),甚至可能不属于高阳方言片这个宽泛的学术范畴。
目前操这种粤方言的地域,全省只有七迳、大衙(已合并到林头镇)两个镇的一部分地方,而且这两个镇相互毗邻,都是客家、福佬、广府三大民系杂居的地方,可想而知,它的范围是多么有限和孤单。这个地域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方言孤岛。然而更大的方言孤岛在包围着这个小孤岛。囿于电白这个几乎纯粹的闽方言的环境,在闽方言(当地人称之为“俚话”)的孤岛中,七迳白话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并不是指它的发音受到了闽语的影响,而是在词汇上大量吸收了闽语词汇。七迳白话有两到三成左右的词汇能在俚话中找到对应的词汇。家乡人称自己的方言为“白话”,说俚话的人则把这种白话称之为“客话”,称“讲白”为“讲客”。这个客话,不是客家话的意思,而是福佬民系为主人,我们这个民系(属广府民系)为客人的意思,这反映了在古时候的电白县,福佬人先入为主,先祖们后入为客的事实,三大民系共同开发了电白。
因为民系的融合,家乡人日常生活中往往双语并用,以白话为主,俚话亦相当熟练。这是语言和民系融合的十分典型的实证,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个十分有学术价值的事实。电白的方言众多,俚话(以霞洞为代表),客家话(以沙琅为代表),海话、军话、旧时正话(以电城为代表),蛋家话(以博贺为代表)都有语言学者做了研究,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和专著,唯独七迳白话,至今还没有人做研究。对于它的形成、归属划分和特点,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我想,这也是因为家乡话范围过小所致,在地域上仅仅相当于一个镇的面积。而且说这种话的人数太少,目前不足8万人。相对本地其它方言而言,实在微不足道,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无庸置疑,作为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和十分珍贵的语言融合的实证,甚至可以称为濒危方言,这种方言研究的空白十分值得去研究。
我很想去做这项工作,但是我没有语言天赋,况且语言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现在普通话的教学已经日渐影响到方言的词汇,家乡很多地道的方言年轻一代逐渐在摒弃。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很多词汇只会用普通话拼读,却不能用粤语读出来。回顾以往,很多小时候会说的方言词汇,现在都已经退化,口语正在让位于书面语,可以说家乡方言词汇流失的现象不可避免。
既然无法对家乡话做考证,只好罗列出一些十分特别的口语词汇,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下面列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口语词汇,至于与其他粤方言说法相同的词汇,一般不作列举。以下所举的例子,也许你都能看得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仔细想想,在日常生活中你却可能不会那样子说,而是别的说法,其实这就我和你的区别。
香与臭系列――家乡话“香”“臭”不分,有如茂名话“买”“卖”不分。乡亲们闻到某种气味,可以说“香某种味道”,也可以说“臭某种味道”,但这是有限度的,中性气味的东西可以“香”“臭”不区分,但真正污秽臭味的气味只能用臭。这也是家乡话中非常特色的地方。茂名话“买”“卖”不分是没有限度的,无论是“买”还是“卖”,都只说“卖”,假设茂名人对你说“卖了某东西”,如果不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判断,你是不知道他是“买”还是“卖”的。呵呵,扯远了,但从这里就知道家乡话与茂名话不是同一路的。
刀系列――“小刀”称为“刀仔”,“菜刀”称为“薄刀”,“大刀、砍刀、柴刀”称为“刀p”。我把这些说法与室友交流的时候,他们笑得肚子直叫痛,因为他们无法明白,这“刀”分出大小和种类犹自可,但是又如何分出性别的?如何会有公和母(p)的区别?虽然很好笑,但我无法解释。
数量系列――“几十万疃唷保不是真的是数量“几十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很多,这是家乡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溜溜”在家乡话中是个很有意思的量词,意思是说“很多很多”,比方说以前家乡经常说但现在很多人遗忘了的――“嗯,人溜溜,贼溜溜,鬼溜溜”,就是说“人很多,贼很多,鬼也很多。”呵呵,很搞笑。
地理系列――称小河为“圳仔”。深圳的大名红遍大江南北,但是“深圳”这个词没几个人真的懂得。“深圳”的本意是指什么?要是你问我家乡人,他们会告诉你,所谓“深圳”,就是一条深深的河流。深圳的得名,其实源于与香港一衣带水的“深圳河”。“山窿”――茂密的树林。“田基”――田中小路。称“中间”为“dōng间头”。
时间与做饭系列:
朝早头――清晨,早上。广州话为“早晨”。“晏咒头”――晌午,下午。“晏咒过”――时间过了下午,或者表示迟到得厉害。“麻\头”――实应作“晚黑头”,夜晚,晚上。 “做到晒黑”――不是干活干到被太阳晒黑的意思,而是干活干到天都黑了的意思,“晒黑”就是“夜晚”。
做饭是“煮朝,煮晏,煮晚,煮汤”,当然也可以用“煲粥,煲饭,煲汤”来代替。食朝――吃早餐,食晏――吃午餐,食晚――吃晚餐。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夕阳晚照在村头的池塘上,妈妈的呼唤远远传来――“快番屋几(企)食晚啊。(快回家吃晚饭)”,温情得很。
出门问候三句话系列――身为家乡人,如果不会这三句话,你不应该出门的。
第一句,“食啊嘛?”――意为“你吃了吗?”。这是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只要碰到隔离邻舍,每见一次,必然要说一次。
第二句,“做乜工啊?”。做工――干活,上班。“做乜工啊?(你去做什么工作?你去干什么活?)”同为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基本要说一次,出门干农活或者在路上见面必然要说一次。
第三句,“去书腻”――去哪里。这个词汇只是音译,正式词汇如何写,还不知道。广州话说“去边道”,茂名话说“去书试”。“去书腻啊?”为家乡人见面最常用的问候之一,一天之中几乎要说一次。
儿女教育五句话系列――似乎是家乡人建立的儿女教育的体系。
第一句,“知头知路”――主动,醒目,知道情况。不用别人出声,自己也知道应该怎样去做,这是家乡父母教育儿女应该怎样做事的必备词汇。
第二句,“执头执尾”――收拾屋里零碎的东西。这也是家乡父母教育儿女应该勤快做家务的必备词汇,主要适用于女孩,早晨起床必备功课,呵呵。
第三句,“夹手夹脚,郁手郁脚”。“夹手夹脚”是教育孩子要有团队合作精神,是“齐心协力,一起动手”的意思。“郁手郁脚” ――不是广州话里的做出一些侵犯别人的不礼貌的动作的意思,而是自己动手去做去帮忙的意思,教育孩子不要懒惰,凡事要自己去做。
第四句,“画公仔画出肠”――话说得太明白,或做事多此一举。父母会经常教导你“毋(母)画公仔画出肠”,意为说话做事应该含蓄点,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
第五句,“督人背脊”――打别人的小报告,背后说别人的坏话。父母会经常提醒你“毋(母)督人背脊”(不要在背后说人长短),既是处事方式,又是品德要求。
骂人四句话系列:
第一句,“车大炮”――假话,吹牛,也可引申为侃侃而谈。家乡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据说广州话也有这个说法,但也只有老广州才能明白。现在的广州话里基本用“吹水”来代替了它的位置。其实“车大炮”是很有渊源的。一些说法是认为来源于古文字或者是象棋。我觉得不然。我认为这个词是近代才出现的。孙中山闹革命之初,无车又无炮,革命成败没有保障,孙中山对民众的承诺也是一句空话,他的政治对手讥笑他在吹牛,所以人称“孙大炮”。家乡人又说“大炮王”,意为满口都是谎话假话的人。
第二句,“断你种、短你命”――原意是一种十分恶毒的骂人的话,诅咒别人短命和没有后代。但在家乡,实际上,仅仅含有责备的意思,连父母都经常这样骂自己的孩子。别人听来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第三句,“粪箕秧、火秧”――同样是咒骂小孩的话,相传以前小孩夭折了就用粪箕装好拿去埋,所以骂人“粪箕秧”是很狠毒的,是咒人死。但是实际上骂人“粪箕秧”其实不是真的恨到入骨非要咒人死,“粪箕秧”现在只是纯粹一句骂人的话,父母生气了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也会骂粪箕秧。
第四句,“马骝仔、马骝婆、马骝精”――广州话有马骝仔的说法,但我敢说绝对没有马骝婆这种说法。家乡话里马骝仔的意思可以是指调皮的男孩子,也可以是仅仅表示对某个男孩子的不屑。马骝婆就是骂女人的话了,无论是少女还是中年乃至老年妇女,如果人家狠狠说你“马骝婆”,你要注意了。但与你相好的好友戏谑地说你“马骝婆”,只是跟你说笑取乐而已。
特色系列:
毋(母)――“无”,与“有”相对,表否定。这是家乡话较特别的地方,既不说北方话的“不”和“没”,又不说茂名话的“印保ǘ磷鳌懊,máo”),亦不说广州话的“唔”。
壳――勺子。制作勺子的原始材料,应该就是植物的硬壳。茂名话说“勺”。家乡人只要这个讲法一出口,别的地方的人一定是莫名其妙。
箸――筷子。广州话虽然有这个说法,但这样说的广州人不多了,几乎用筷子代替了。
望火――煮饭的时候,看着灶火,不让火熄灭和烧了其他地方或者是掌握好火候。望火是家乡的小孩子必修的课程,年幼的孩子干不了什么,还未能“帮手(帮忙)”,父母就经常叫孩子“得闲(有空)”去“望望火”。
飞头――理发,也作“剪头”。乍听上去像是杀头,似乎是清皇朝高压民族压迫政策的残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讲笑)。其实就算是头发,家乡也只说“头毛”。
颈渴――口渴。有时候也使用“口渴”。俚话称为“喉渴”。口渴的同时也就是喉咙干渴和颈部干渴的同时。真是无奇不有,到底是“颈渴”还是“口渴”还是“喉渴”?我看就算是医学的专业人士也分不清楚。
鸡春――鸡蛋。“春”表“蛋”,鸭春为鸭蛋,以此类推。外地人初次听的时候简直不明白你讲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这几乎是家乡词汇独一无二的地方,凭这个就可以判断出是不是家乡话。
做米乙――米乙是米粉做的一种过节用的食品。这一种食品,俚话统称为“buǎ(没有文字表述)”,潮汕地区称为糍粑,茂名话也叫米乙,但发音和家乡话不同。小时候隔离村极少数人甚至有一种说法,不知语出何处,直接叫做“妈”。称做米乙为做妈,感觉一定很怪。
趁嘘――用北方话解释就是“赶集”。广州话说“上街、逛街”,虽然意思相近,但趁嘘不同于上街,上街的主要意思是到街上购物游玩,而趁嘘的主要意思农村人到镇上做买卖。
肚疼――顾名思义,是说肚子疼痛。但这里的主要意思,却不是说肚子疼,“好肚疼凇辈皇恰八疼得厉害”的意思,而是“非常喜欢、疼爱她”的意思,一般用于形容长辈对晚辈的喜爱。
书房――上学,“去书房”意为“去上学”,这是十分文雅而且很形象的说法。俚话也是用这个词汇。出门在外,除了吴川话和化州话,我很少听到这种说法。
作仔――鸟类的统称。实应作“雀仔”,但家乡人发音却为“作仔”,这个讲法茂名话也有,但家乡话的发音,茂名人不晓得。
去哨、去料 ――“去哨”不是去放哨,“去料”也不是工厂里的来料加工,这两个词都是“去玩”的意思。
睇过――在广州话里有“看一看”的意思,在家乡这个说法也有这种意思,但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先等一等,先看一看情况再说”。
生丁―陌生、生疏。这个讲法估计广州人听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茂名人有一部分人能听懂,例如羊角那边。
做屋――盖房子,俚话也有这个词汇。广州话为“起屋、起楼”。这个说法估计听过的人不多。
复餐――表面意思是“加餐”,实际意思却是“夜宵”。只能用于吃完晚饭后的加餐,其余加餐则不能用。
失魂――晕倒,精神恍惚。
抵力――生病或者很难受。生病原本就是很耗力气的事情,故说“抵力”。而有时候想表达很难受的感觉或者很看不惯(广州人说“难顶”)也可以说抵力,比如:我见到冢假设是丑女)就抵力(我见到她就难受)。
灶下――厨房。俚话叫“灶庐”,都几形象的。
火水――煤油。因为使用煤油点灯的人不多了,这个称呼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
līn地――撒赖,哭着在地上不停地滚动。小孩子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经常向大人表现出来的动作。
兑命――不是要与人交换性命,而是以撒赖为要挟,以达到目的。小孩子经常向大人“兑命”。
火起――不是发生火灾,而是生气了,又经常说“发火”,也经常说“火滚(恼火)”,甚至于“把几火(一肚子火)”。
够担――形容两个人关系很好,气味相投。香港粤语叫“一担(声调:阴平,名词)担(音调:去声,动词)”。
āo wū ――发音如此,没有文字。这是大人哄三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形容小孩子疼的感觉。
恶教 ――难教育,不听话,说了也不听。
恶刮――态度恶劣。也经常说“恶死”。“恶刮到死”意思是“态度差到极点了”。
多口――口只有一个,是不会多的。“口多多”是指“八卦,说是非”。
浪冻――指让高温的物体温度降下来。
琼干――特指让液体挥发掉或者凝固起来。
捞食――不是“搅拌食物”,而是“谋生”的意思。
索烟――不是向人索要烟,而是抽烟,广州话为“食烟”。
交关――事态严重,同“弊”。广州话不会这样,他们说“大镬”!
银包――钱包,广州话作“荷包”。银纸――钱,钞票。
折秃――做孽,遭遇悲惨。广州话叫折堕。
注意――小心。
混帐――不像话,不同意,反对,乱来的。
嬲气――生气。甚至“嬲爆胆(气冲冲)”。“谷气”――“憋气”。至于“激气”,则是“心里有气”。
特停――故意的。广州话说“专登”。
心水――“心意”。“心息”就要“死心”了。“心抱”却是“媳妇”。 “收心”是要“专心一点,或者是死心了放弃吧”,“心落”是说“放心了”。
huàn大――养大 。
yào hái――只是谐音的音译,没有文字。意思是“抓痒”。
压萨――没有文字,音译,但不是很谐音。意思是“吝啬”,广州话说“孤寒”。家乡也说“孤寒”,除了有这个意思,还有“家境寒苦”的意思。
扫山――不是到山上去打扫清洁,而是去扫墓。
混人――不是出来混的人,而是“欺骗人”。
摞雷――找麻烦 。“雷”其实应做“来”。“自己摞雷”意思是“自己找来的麻烦”。
爱嘛?――要吗?要不要?
例头――里面。“下低头”――“下面”。而俚话说“里面”和“下面”都是说“底头”。
做得――行,可以,表示肯定、同意、承诺。
浪衫――晾衣服 。
日头――太阳 。
屈头――转弯。
好劲、好叻――很厉害。这和茂名话明显不同,茂名人说“好强”。
头壳――脑袋。
假衣车――意为“假装”,装模作样。为什么这样说,我至今不明白。
打白脚――赤着脚,不穿鞋子。小时候我经常打白脚,家人恐吓我说会“大脚板(脚底会变得很大)”。
打白手――两手空空。去“探”(看望)“人家(别人)”,“打白手”是被视为不礼貌的表现。这和上面的“打白脚”字面上好像很相近,其实意思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
细蚊仔――小孩。茂名话叫“细弄”,俚话叫“细弄仔”,广州话叫“细路哥”。
猛去咧――你够胆(有胆量)就去吧!这是家乡的父母恐吓孩子、不让孩子去做某些事情的必备语录。
喊乜人――“你喊乜人啊?”不是对着什么人叫喊的意思,而是“你找谁?”的意思,同时又是“你安排谁?”的意思。
托大脚――拍马屁。现在很多人只会说“擦鞋”了。
打乞超――打喷嚏。
偷盐蛇――不是什么蛇,而是壁虎。因为它经常在厨房盐煲旁边出没,农村人以为它会偷吃盐,其实偷盐蛇不偷盐。
走无尾、搏命走――拼命走。广州人说“走甲唔头”。
捞油水――占便宜,着数。
毋(母)着数――不值得。没有便宜占。
毋(母)著衫――赤着上身。广州话叫“打大赤肋”。
落雨咪――下着毛毛雨。
钱蚕舂(音译)―― 广州话叫“教剪踏 ”,北方话叫“剪刀石头布”。
XX转――晕头转向。
一阵仔――一阵间。
眼崛崛――瞪大眼睛,表示不满或生气。“眼蛇蛇”、“眼够够”则是说“不敢正视,只好斜视着”。
好怕擂擂――态度恶劣得很,使人害怕。
ài交打交――吵架打架。
nòng kiào kiào――全烧焦了。
稀pá lá――稀巴烂。
打百分――打扑克。又叫“打牌”,“打pie”。
收起身――藏起来,整理放好。
茄呢茄liě――古里古怪 。
落水踏帝――下着雨,湿漉漉的。
吟吟寻寻――有时候也说“罗罗嗦嗦”,意为喋喋不休,说过不停。
执人口水――又一说法是“口水王”,有时候也说“学口学舌”。都是同一个意思,意为鹦鹉学舌,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
好怕到死――不是“很害怕死”,而是“害怕到要死”,形容装扮很难看,面色很难看,样子很令人害怕(广州话“得人惊”)等等。
以上这些,只是家乡方言词汇的一个断面。当然还有很多经典的词汇,一时之间数之不尽,要做这个整理工作,实在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很多口语,有音无字,无法用文字表达出来,粤方言又几乎出口就是古汉语、古文字、生僻字,就算有字也没能认出几个来,更写不出来,以致很多生动活泼的家乡话没法表述。一种方言最重要的其实是语音,是凭藉着发音来与其他方言相互区别的,而词汇相对来说则显得没语音那么重要。由于个人能力不足,家乡话的语音与其他粤方言的区别和归类只能有待有心人去做,它的起源和演变也有待探究。我对家乡方言词汇的介绍也到此为止,希望大家中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