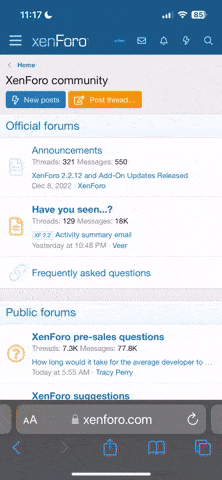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 注册
- 2004-08-16
- 帖子
- 7,441
- 反馈评分
- 65
- 点数
- 71
余富兵的右手没有抓住他心爱的手机,因为他的右手已经和手机一起掉在了地上。他的妻子不知道,还在前面拼命追赶5名抢走她100元钱的持刀歹徒。“别追了,我的手被砍掉了!”余富兵朝妻子嘶声高喊……
这是2004年12月17日夜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水口附近的马田北路的一幕。为首的砍手歹徒叫许国亮,18岁。案发5天后的夜里,当抓捕他的警察把他从广西家中的床上拖起来时,感觉许国亮的体重很轻,简直就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单薄少年,在铐住他的瞬间,他一点都没反抗,可能是当时还没睡醒。
但深圳警方查明,就是这个瘦瘦小小的许国亮,和19名成员组成一个抢劫团伙,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
在公明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一年时间内先后做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
这些抢劫者均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广西天等县人称他们为“上映帮”。
“上映帮”的成员又基本来自同一个村庄――上映乡温江村。温江村,深圳向西略偏北一千余公里处,距天等县城40公里,距中越边境30余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已经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的警方手中,有两对还分别是亲兄弟。但熟知“上映帮”的知情者称,目前在广东抢劫为生的温江村年轻人远不止这个数,而是多达上百人!
许国亮被抓后交代得更为干脆利索:“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边抢东西。”温江村的知情者透露,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们失业,也很有可能被“上映帮”吸纳进去。
家
“今年春节儿子总该回来了吧”
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远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因何成了劫匪的故乡?一切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谈起。根据天等县警方的了解,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他于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帮”曾与深圳宝安警方发生过数次枪战。警方推测,“上映帮”的枪极有可能是从相距不远的越南那边贩运过来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认为:“赵民显给到广东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是他开的路。”
赵民显家在温江村山岱屯,村中心村委办旁。赵家的邻居、村委书记冯成金称,赵从小看起来老实内向,因为家里穷没读完小学。赵民显家住的是那种老式土房,他的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父母一样,想为儿子造间新房。所以他的父亲去打石头赚钱。结果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大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根本赔不起,造房梦也破灭了,所以全家都跑到了广东去打工。游荡一段时间后,赵民显也赴深打工。但到了2002年时,赵民显已蜕变为深圳市公明镇有名的“悍匪”了,数次和警察发生枪战。
上映派出所介绍,赵民显在2001年左右开始慢慢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后,他已经是初具气候的“上映帮”老大。不但抢劫,还在公明、松岗一带的长途汽车站收保护费,并数次在和其它黑帮的争斗中死里逃生。但他终于没有逃过牢狱之罚,2003年4月被广东警方抓获,2004年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只有赵民显的伯伯留守在家,有时过来看看这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为了增加这间老房子的人气,老人在赵民显家门口挂了一串金黄的玉米棒子,在冬天的阳光下落寞地晃动着。
从赵民显家步行十余分钟乡间小路,就可以到黄海清家。黄海清属于“二进宫”,他是2004年初满刑释放后赴深,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抢劫被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批捕。村委书记冯金成不忍心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黄海清的父亲黄尚美手中,所以黄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儿子被抓的事。他埋怨着儿子:“家里太困难了,海清快一年了还没寄回过一分钱。”
黄家的黄泥土房已历经祖孙四代了,外墙龟裂横竖,有的缝已经能插入一只手掌。几年前,黄尚美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用光了家里的钱,也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
黄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垫的。因为没有好一点的床,所以黄尚美说两个儿子从十多岁后就没在家里睡过。因为没钱换破了的瓦片,到了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黄海清家唯一值钱的是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黄牛,老黄牛已经差不多没有力气耕田了,但他们家买不起小牛犊。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亩多的水田和一亩多的旱田,全年只有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黄海清的母亲黄玉芬说最愁的是过节,过节时常常发愁怎样找钱买肉。他家一年中吃肉的机会只有两三次。
打击黄尚美的不只是疾病与贫困,小儿子黄海珍在两年前离家出走后至今没有音讯。两年多前,黄海珍参加了新兵招征,体检合格。他以为可以实现当兵梦了,但最后因为他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刷下。他抛下一句“家里太穷,我要出去打工赚钱”就出走了。“他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都怪我们,没有钱让他念初中,本来他一定可以去当兵的。”母亲黄玉芬显得很懊悔。
因此大儿子黄海清更成了黄家的盼头,现在两老盼着黄海清回家过春节。
“只要他回家过年,哪怕他一分钱没赚,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高兴的。”黄尚林说得有些黯然。
从黄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许国亮家。许国亮家的砖瓦房是靠他父亲打矿赚来的。许国亮的母亲看到陌生人,眼睛里有些诚惶诚恐。许国亮的伯母道出了原因,上个月许国亮在家中被警察抓走后,许国亮的母亲现在一听到“广东来的”就会怕得发抖。
许国亮家的父亲和哥哥都到邻傍的土湖乡挖锰矿去了,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许国亮的哥哥也曾经因为涉嫌抢劫被深圳市公明派出所抓过。但他的母亲认为两个儿子在家里都很听话,她至今不相信那么瘦弱的儿子会去抢劫,还会残忍地砍掉别人的手。“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乱承认的。”许母显得忿忿不平。
许母所不知道的是,不只是许国亮,和许国亮一起经常在抢劫时砍手砍脚的其他18个人也一样的瘦弱。据说一开始调查这些抢劫者时,连警察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瘦小,这样单纯,像没长大似的,怎么下手就这样狠呢”。许国亮的供述则称:“我们拿刀,而且很多人一起。不肯给的就砍了。”
许国亮的卧室床边贴了几张个人照,看起来果然瘦瘦弱弱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这可能是后来他告诉警方的他最想念的女朋友,“她还不知道我干这事,也不知道我进来了”,“我害怕她看不起我,害怕她和我分手”。
而据上映派出所最早铐住许国亮的警察回忆,他搜查许国亮的枕头时没有搜到刀枪,却摸到一张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体检单。虽然看起来已经皱皱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这说明许国亮曾经非常想当兵,并且一直怀着这个梦想,所以才会一直保存着这份体检单。但村委书记冯成金说,即使体检合格,许国亮也当不了兵,因为他连小学都没毕业。
许国亮家旁边不远是许国亮堂兄许国定的家。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穿着暗蓝的灰旧布袄的赵玉梅和邻居们坐在许国定伯父家的灶堂边烤火,因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闪动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
用温江村人的话来说,赵玉梅是个命苦的女人。丈夫在许国定不到十岁时就因病去世,此后她所有的心血放在了维持生计与抚养孩子上。但孤身的母亲倾尽全力也只能供许国定读到小学四年级。四亩稻田成了赵玉梅赖以生存的血脉,即使两个儿子没在身边,她还是以六十之躯照料这些稻子。只有像这些寒冷的冬天,坐在这样的灶火旁取暖时,才是她一年中最闲暇的时光。
现在老大许国干在大新县土湖乡那边打矿,每个月可以回家一两趟,所以她现在特别挂念二儿子许国定,“这个儿子真是有点不听话,出去也快两年了,连个信也不捎回来。今年春节他总应该回来了吧。”赵玉梅愁苦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她曾经向所有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温江村人问许国定的下落,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愿意告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
村
“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
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
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
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
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
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
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
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
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
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城
“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
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
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
这是2004年12月17日夜发生在深圳市公明镇街道办合水口附近的马田北路的一幕。为首的砍手歹徒叫许国亮,18岁。案发5天后的夜里,当抓捕他的警察把他从广西家中的床上拖起来时,感觉许国亮的体重很轻,简直就像个还没有成熟的单薄少年,在铐住他的瞬间,他一点都没反抗,可能是当时还没睡醒。
但深圳警方查明,就是这个瘦瘦小小的许国亮,和19名成员组成一个抢劫团伙,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仅17岁,采用砍手、砍脚等作案手段抢劫。
在公明街道办合水口、马田一带,一年时间内先后做下25宗劫案,砍伤路人12名,抢劫了大量手机、手提包和现金。
这些抢劫者均来自同一个地方――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深圳民间称他们为“砍手党”,广西天等县人称他们为“上映帮”。
“上映帮”的成员又基本来自同一个村庄――上映乡温江村。温江村,深圳向西略偏北一千余公里处,距天等县城40公里,距中越边境30余公里。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04年就已经有40余名温江村青年落入了深圳、东莞、佛山、汕头、云浮等地的警方手中,有两对还分别是亲兄弟。但熟知“上映帮”的知情者称,目前在广东抢劫为生的温江村年轻人远不止这个数,而是多达上百人!
许国亮被抓后交代得更为干脆利索:“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边抢东西。”温江村的知情者透露,目前温江村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们失业,也很有可能被“上映帮”吸纳进去。
家
“今年春节儿子总该回来了吧”
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远在广西的一个小村庄因何成了劫匪的故乡?一切要从一个叫赵民显的人谈起。根据天等县警方的了解,赵民显算得上是温江村的“匪帮教父”,他于2004年被深圳警方判处无期徒刑,之前他所率的“上映帮”曾与深圳宝安警方发生过数次枪战。警方推测,“上映帮”的枪极有可能是从相距不远的越南那边贩运过来的。上映派出所一位负责人认为:“赵民显给到广东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开了个坏头,后来温江村年轻人抢劫成风,是他开的路。”
赵民显家在温江村山岱屯,村中心村委办旁。赵家的邻居、村委书记冯成金称,赵从小看起来老实内向,因为家里穷没读完小学。赵民显家住的是那种老式土房,他的父亲和村里的其他父母一样,想为儿子造间新房。所以他的父亲去打石头赚钱。结果在一次爆破作业中,大石头压死了两个雇工,法院判决赵家向受害者赔偿6万元。赵家根本赔不起,造房梦也破灭了,所以全家都跑到了广东去打工。游荡一段时间后,赵民显也赴深打工。但到了2002年时,赵民显已蜕变为深圳市公明镇有名的“悍匪”了,数次和警察发生枪战。
上映派出所介绍,赵民显在2001年左右开始慢慢拉一些温江村年轻人下水,到了2002年前后,他已经是初具气候的“上映帮”老大。不但抢劫,还在公明、松岗一带的长途汽车站收保护费,并数次在和其它黑帮的争斗中死里逃生。但他终于没有逃过牢狱之罚,2003年4月被广东警方抓获,2004年被判无期徒刑。
现在,只有赵民显的伯伯留守在家,有时过来看看这间空无一人的老房子。为了增加这间老房子的人气,老人在赵民显家门口挂了一串金黄的玉米棒子,在冬天的阳光下落寞地晃动着。
从赵民显家步行十余分钟乡间小路,就可以到黄海清家。黄海清属于“二进宫”,他是2004年初满刑释放后赴深,2004年11月23日,又因涉嫌抢劫被深圳宝安区检察院批捕。村委书记冯金成不忍心把批捕通知书送到黄海清的父亲黄尚美手中,所以黄尚美至今仍不知道儿子被抓的事。他埋怨着儿子:“家里太困难了,海清快一年了还没寄回过一分钱。”
黄家的黄泥土房已历经祖孙四代了,外墙龟裂横竖,有的缝已经能插入一只手掌。几年前,黄尚美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用光了家里的钱,也让他丧失了劳动能力。
黄家的床是用竹片和稻草作垫的。因为没有好一点的床,所以黄尚美说两个儿子从十多岁后就没在家里睡过。因为没钱换破了的瓦片,到了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黄海清家唯一值钱的是那头养了十年的老黄牛,老黄牛已经差不多没有力气耕田了,但他们家买不起小牛犊。家中的收入主要靠三亩多的水田和一亩多的旱田,全年只有三四百元左右的收入。黄海清的母亲黄玉芬说最愁的是过节,过节时常常发愁怎样找钱买肉。他家一年中吃肉的机会只有两三次。
打击黄尚美的不只是疾病与贫困,小儿子黄海珍在两年前离家出走后至今没有音讯。两年多前,黄海珍参加了新兵招征,体检合格。他以为可以实现当兵梦了,但最后因为他只有小学学历而被刷下。他抛下一句“家里太穷,我要出去打工赚钱”就出走了。“他没告诉我他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都怪我们,没有钱让他念初中,本来他一定可以去当兵的。”母亲黄玉芬显得很懊悔。
因此大儿子黄海清更成了黄家的盼头,现在两老盼着黄海清回家过春节。
“只要他回家过年,哪怕他一分钱没赚,什么也没买回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高兴的。”黄尚林说得有些黯然。
从黄海清家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许国亮家。许国亮家的砖瓦房是靠他父亲打矿赚来的。许国亮的母亲看到陌生人,眼睛里有些诚惶诚恐。许国亮的伯母道出了原因,上个月许国亮在家中被警察抓走后,许国亮的母亲现在一听到“广东来的”就会怕得发抖。
许国亮家的父亲和哥哥都到邻傍的土湖乡挖锰矿去了,一般一个月才回家一趟。许国亮的哥哥也曾经因为涉嫌抢劫被深圳市公明派出所抓过。但他的母亲认为两个儿子在家里都很听话,她至今不相信那么瘦弱的儿子会去抢劫,还会残忍地砍掉别人的手。“这小孩子一定是不懂事,乱承认的。”许母显得忿忿不平。
许母所不知道的是,不只是许国亮,和许国亮一起经常在抢劫时砍手砍脚的其他18个人也一样的瘦弱。据说一开始调查这些抢劫者时,连警察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这样瘦小,这样单纯,像没长大似的,怎么下手就这样狠呢”。许国亮的供述则称:“我们拿刀,而且很多人一起。不肯给的就砍了。”
许国亮的卧室床边贴了几张个人照,看起来果然瘦瘦弱弱的。旁边还贴着一张女孩子的照片。这可能是后来他告诉警方的他最想念的女朋友,“她还不知道我干这事,也不知道我进来了”,“我害怕她看不起我,害怕她和我分手”。
而据上映派出所最早铐住许国亮的警察回忆,他搜查许国亮的枕头时没有搜到刀枪,却摸到一张2003年的征召新兵的体检单。虽然看起来已经皱皱巴巴,但保存得很完整,这说明许国亮曾经非常想当兵,并且一直怀着这个梦想,所以才会一直保存着这份体检单。但村委书记冯成金说,即使体检合格,许国亮也当不了兵,因为他连小学都没毕业。
许国亮家旁边不远是许国亮堂兄许国定的家。2003年时,许国定在飞车抢劫时撞警察拒捕而被警方击毙。但许国定60多岁的母亲赵玉梅至今还以为儿子在深圳打工。
穿着暗蓝的灰旧布袄的赵玉梅和邻居们坐在许国定伯父家的灶堂边烤火,因为她家的土房子塌了。闪动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皱纹的脸和灰白的头发。
用温江村人的话来说,赵玉梅是个命苦的女人。丈夫在许国定不到十岁时就因病去世,此后她所有的心血放在了维持生计与抚养孩子上。但孤身的母亲倾尽全力也只能供许国定读到小学四年级。四亩稻田成了赵玉梅赖以生存的血脉,即使两个儿子没在身边,她还是以六十之躯照料这些稻子。只有像这些寒冷的冬天,坐在这样的灶火旁取暖时,才是她一年中最闲暇的时光。
现在老大许国干在大新县土湖乡那边打矿,每个月可以回家一两趟,所以她现在特别挂念二儿子许国定,“这个儿子真是有点不听话,出去也快两年了,连个信也不捎回来。今年春节他总应该回来了吧。”赵玉梅愁苦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她曾经向所有从深圳打工回来的温江村人问许国定的下落,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愿意告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
村
“他们在家都是好人啊”!
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许国亮生活的这个温江村普遍贫困,实际人均年收入才四百元左右。地理位置也“很山”,从县城到村里虽然只有40公里路,却要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到温江村需经过几段当地人所谓的“三跳路”,即“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胸里跳”。
整个温江村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有十个屯,共600余户人家,3000多人。村中心的前面叫前山,后面叫后山,这些山都是广西特有的石灰岩质的石山,树木稀少而矮小,但拔地而起的石山形态雄奇险峻。从山上流下来经过村前田地的一条小溪叫“温江”,这也是温江村名字的由来。
这条小溪流到村中心的地方积成了一口小池。这口小池是温江村砖厂挖砖泥挖出来的。这个砖厂是远近村庄唯一的“工业”。
砖厂旁边,是温江村小学,这些后来被称为“悍匪”的人都曾在这个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的两层教学楼是依赖1997年世行的扶贫基金建起来的。此前包括许国亮在读时,教室都设在快要坍塌的土垒危房中。但旁边的八个教师宿舍至今破旧。张有勋校长介绍这是十年前老师们自已做水泥砖建起来的。门破旧不堪,屋内阴暗潮湿,每间宿舍才十余平方米,同时兼做办公室和食堂。
十余名小学老师中,几名代课老师每月工资223元,一般有事业编制的老师工资在500元左右。只有张校长的工资最高,因为他已经是有数十年教龄的高级教师,所以有约900元左右的工资。
回忆起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在深圳或被击毙,或被判刑,或被抓捕的温江年轻人,张有勋校长很沉重:“他们读书时和其他小孩没什么区别,长大了后在家里也都是很老实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那里(指广东)就变坏了。”张有勋认为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家里穷,上不起学,很多人小学都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又要吃饭,这可能成为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事实上,上映乡派出所提供的2004年“犯事”的20名温江村年轻人的学历显示,几乎没有人上过初中,大多数人只读到小学三四年级,赵民显、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的学历都在小学四年级以下。
在2000年春节时,这所小学的老师们为外出广东的温江青年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应这些打工青年的主动要求,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和“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个地名。老师们回忆,这些年轻人到了广东后因为连自己的名字和家乡地址都不会写,被不少工厂拒收。2004年底的时候,一个在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他已经辍学的弟弟重新回温江小学读书。“因为他自己尝够了不会写名字找不到好工作的苦,知道应该让弟弟多读几年书才能在广东找到好点的工作。”张有勋校长分析。由于近年广东对打工者的学历要求略有提高,所以温江村小学的老师们发现,这个小学的辍学率已基本缩小到零。但据了解,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在温江村仍然不到40%.而升初中后辍学去找工的学生在整个上映乡也很多。据上映乡中学反映,初二年级每年春节后都会有四五十人辍学打工。
村支书冯成金和村校长张有勋共同担心的另一个教育问题是,家里空巢了,孩子们在家里缺乏管教。冯成金认为,不少“犯事”的温江村年轻人,当年他们读小学时基本都是这样,所以出现了“从小家教不好”的情况。这种现象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呈愈演愈烈,因为“现在呆在家里就一分钱也赚不到”。在记者抽样调查的温江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共70多名学生家庭中,父母都留在村里的只有两户人家,另外32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广东打工去了,43户人家的父母一方到温江村旁边的大新乡挖锰矿去了,还有7名学生的父亲去挖矿母亲去广东打工。
在小学旁边就是村委办公室,这是一间低矮的平房。“我们这里太穷,两个村委委员不干了,都打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老头子了。”50多岁的村支书冯成金叹息。他形容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现在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冯成金介绍,十多年前,温江村有力气的人基本都去广东打工,所以村里最漂亮的两座房子都是早年打工的人赚来的。但现在温江村人感到,在广东打工已经越来越赚不到钱。十年间物价涨了不少,但广东的工资和十年前一样,甚至还没有十年前高。所以,全村大约70%的青壮劳力都打矿去了。
因为挖矿每个月少则能赚八九百元,多则能赚一两千元。温江村232座砖瓦新楼房中,冯成金介绍,90%以上都是打矿赚来的。
但这种赚钱的活并不是像许国亮这样的年轻人们愿意干的,因为打矿给他们留下恐怖的记忆。
黄尚林20多岁的儿子黄海亮就在打矿中被压死。2002年将近年关时,新婚不久的黄海亮为了还结婚所欠的几千元钱,决定受雇于大新县土湖乡的私矿老板,但几天后他就殒命于塌方的矿洞中。“命不值钱啊,老板只给了八百元安葬费。”五十多岁的黄尚林坐在到处是裂缝的黄泥土房里一边回忆一边叹气。这件事使他下定决心,决不让第二个儿子再去打矿。所以他的二儿子现在到广东打工去了。
几年下来,全村打矿被压死的人已经上升到16人。村里在打工与打矿方面也出现了分野,有了家室或者马上想成家的青壮年男子为了养家糊口,更愿意去冒死打矿。而像许国亮这样20岁左右的年轻人,害怕打矿的风险,向往城市的生活,所以喜欢到广东的大城市里去搏一把。至于他们是如何在广东“搏”的,多数父母就不得而知了。
对“温江村现象”,上映乡政府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认为,这可能和上映乡,尤其是和温江村人强悍的山民性格有关。据他介绍,前几年,上映乡的一些村与村之间,村内的屯与屯之间,都有打架的传统。一言不合,就全村出动,青壮年冲在前面,老少们在旁边助威。许多村民也习惯于带着砍刀去赶集。直到后来乡里开始对这些乱象全面整顿,才基本做到了村与村之间不打架,管制刀具不现身。“但这种戾气是需要通过教育慢慢来化解的,整顿只是治标。所以这种戾气可能也一部分地被这些小年轻们带到了广东。”这位负责人认为。
但事实上,走在温江村,除了能感受到这里的贫困与淳朴外,并没法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戾气”。这里的村民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没有”,如果说“还没吃”,那么他家里不管多贫困,也一定会被请吃一顿。村中至今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风,村民家的房门基本上都是随意开着的。一个叫黄彩妹的12岁小女孩因为家中很穷出不起路费,所以从没去过县城,记者知道后给了她几元钱路费。结果她60多岁的奶奶知道后,马上从所住的屯里走了半个小时的路把钱送到村支书冯成金手上,说“咱穷人也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后来冯成金反复解释,她才含着泪收下。
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个村2004年在广东“犯事”的四十余年轻人中,只有一名叫黄海清的25岁年轻人曾在上映乡派出所有过案底――盗窃摩托车。
而其他人,不管在他们的村人眼中,还是当地政府眼中,都曾经是“老实人,良民”。温江村在2004年没有一宗刑事案子,整个上映乡在2004年只有不到十宗的刑事案子,整个人口40余万的天等县,2004年全年才299宗刑事案子。
天等县自2000年来,连年被评为广西或崇左市的社会综合治理模范县。
“他们在家时都是好人啊,为什么到了广东几年就变坏了呢?”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冯成金到乡里、县里政法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一个令他们困惑不已的问题。
城
“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
进城后,与自己这帮从小玩大的朋友们不同,阿星没有混黑社会,而是选择辛苦打工。他很珍惜手上这份每天干12小时每月300块钱的活,很怕自己如果失去工作,走投无路,也会跟着老乡们一起去抢
从广东东莞打工回村休息的阿星,给记者念了一句在外出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中流传的顺口溜:“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抱着美女睡。”
阿星面相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他和许国亮、许国定、黄海清等“犯事”的同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但没有像他们那样去“混黑社会”,而是做了一名辛苦的打工者。
从15岁到19岁,阿星一直在东莞一家工厂的重复劳作中度过,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六七天外,整年只能休息一两天。
但即便这样,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三百多元。“对此,他有点难为情:”每年过春节,我都没钱给爷爷奶奶送礼物,觉得很没面子,活得很窝囊。“
每说一句话,阿星几乎都要咳嗽一次。“厂里的工作太累,永远觉得睡不够。所以身体被搞坏了”,他解释。“这次能这么早回村,就是因为身体扛不住了才被准假。”和他一同回家的另一名同村人则是因为在打工时吐了血――“他用嘴给机器的油管吸油,结果被机油呛伤了肺,又没钱医,只能先回来休养一下。”阿星介绍。
阿星所在的那个厂,有十五六个温江村人,平时除了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就是睡觉,“连打牌的时间都没有。如果想喝酒,也是和老乡在一起吃饭时喝点啤酒”。他最大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份只要八小时的工作,“工资能有500元就满足了,可惜自己文化低,太难找了”。
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很能理解许国亮为什么从工厂里出来,“因为这(工厂里)有点不像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原来都是好人,走上这条路是不得已。如果他们能找到份稍稍好点的工作,怎么愿意去走这种不归路呢。”
阿星记得,许国亮等一批在“干那种事”的温江村人,去年曾数次来东莞找他,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过得像流浪汉一样。“厂里管得太严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帮他们安排住”,但出于老乡义气,阿星拿出身上仅有的七八元钱,买了四碗炒米粉给他们吃,他们都吃得狼吞虎咽。“我对他们很好,他们对我也很好的,从来没有要求我一起和他们干,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有这么一份工作不容易”,阿星说:“这真是条不归路”。在温江村一百多个抢劫者中,阿星只看到有一个人收住了手重新做人,“因为那样来钱太容易,有了第一次就想干第二次,一直到被抓去或者到被枪毙为止”。
据阿星了解,“许国亮们”的生活是“饿时饿死,撑时撑死”。“他们一百多个人,一人一天抢七八部手机是家常便饭,常常一天花上一万两万元”,“有了钱也不往家里寄,家里人还以为他们在深圳打工工资太低,很辛苦”。事实上,这批劫匪们却基本把钱用在了花天酒地、上网玩游戏和嫖妓上。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过得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钱的时候就特别想玩得疯狂一些。”阿星的这些描述,与许国亮向警方所供述的内容恰好相符。
阿星没法理解的是这些朋友们抢劫时的残忍手段:“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是怎样下手的,我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那么狠。”但谈到对城市的看法时,阿星又想给这种残忍的产生作出一点解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现在,留给“阿星们”的环境愈发困难,这种困境源于温江人自己制造的恶性循环。
在深圳和东莞,温江人的名声越来越差了。许多工厂甚至一看男性应聘者是天等县上映乡的,就不敢聘用。像温江村小学校长张有勋的一个儿子就碰到过这种情况,直到他拿出中专学历,那个工厂才接收了他。这种情况使更多新来广东的温江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在生存难以为继的时候,很容易接受“上映帮”的召唤,加入抢劫群体,导致上映人和温江人的名声更加差下去。
目前,据阿星所知,在东莞深圳正经打工的温江村年轻人(不保括那些来深打工的中老年者)只有三十多名,而横行在珠三角抢劫的温江村人却有一百多人。这让阿星特别珍惜手上的工作,准备病一好就回厂里做工,“怎么样也比抢劫强啊”。
“但我很怕,很怕最后也会撑不住走上他们的路。所以我想到一个没有老乡的地方工作。”说到此处,阿星突然又来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
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去年底先后发生在广州与深圳的砍手抢劫事件,令人震惊又发人深思。而当媒体披露深圳的砍手案背后有一个人数很大的“砍手党”,其成员竟然来自同一个贫困的广西村庄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即直达“砍手党”的老家,了解抢劫群体“村庄化”的社会学成因。
下这个决心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据我当时推测,这个村庄可能是一个排外强悍、道德崩溃、不以犯罪为耻的混乱社会,甚至带来人身危险。一直到我抵达这个村庄后,才惊讶地发现自己想错了。
上映乡温江村人,热情好客,不欺生人,从村到全县治安也都不错,有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乡村社会遗风。甚至,那些在外残忍的人,回到村里后照样孝敬父老、种田挖矿,呈现出明显分裂的行为特征。
那么,是什么使这群成长于淳朴之地的年轻人,到了城市后却变得张牙舞爪、肆意妄为?
当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当一次又一次地行走在这个村庄,倾听人们诉说悲剧与命运,绝望与希望时,答案也开始显山露水了。
乡村贫困对他们的伤害依然是最根本性的、最直接的莫过于因贫困使他们从小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幼年时期就都外出打工去了。我们手头掌握资料的20名温江村抢劫者中全部是小学学历,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
与生存现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逐渐形成的城市化生活观念。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对此现象,中国社科院教授刘建国在发行《2005年社会蓝皮书》时有过评论:“不只是这些问题(指中国城市治安问题),我们担心地是(农村)集体情绪的仇恨城市。”
在离开这个小山村前,我给温江村小学里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题目叫“知识改变命运”。虽然我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读完初中,但还是想给他们一个希望。那天晚上,我和贫寒乡村老师们一起住在破旧的宿舍里,一起烤火,一起喝酒。当聊到这些孩子们和城市孩子一样的好奇心与梦想时,我们开怀大笑,心有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