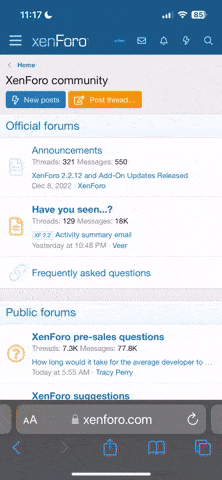狐狸
流浪在别处
- 注册
- 2004-12-17
- 帖子
- 2,587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61
- 年龄
- 37
狐狸
作者:苏童
从前香椿树街没有一所学校,人们后来常常提起的红旗小学是由废弃的教堂改建的,那
时候来自异域的传教士早已远离这条世俗的没有信仰的街区,教堂附近杂草丛生,酿酒厂的
残渣垃圾被随意地堆放在礼拜堂里,而传教士曾居住过的青砖小楼里住着酒厂的一群粗蛮的
外地民工,他们把楼梯和凉台弄得尿迹斑斑污秽不堪,红旗小学来之不易,那些创业时期的
老教师后来习惯于对新来的教师回忆当初艰苦办学的情景,关于狐狸的故事也是那些白发教
师在课间休息时最喜欢的话题。
倪老师初到学校就很引人注目,她是被红旗小学的第一任校长郑老师领进简陋的办公室
的。人们记得她梳两条长辫,辫梢上扎一对豆绿色的蝴蝶结,她的裙子和随身带来的皮箱也
同样是雅致耐看的豆绿色的。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立刻注意到了倪老师的美丽,不仅由于她
的天生丽质和脉脉含情的微笑,更由于她的谈吐举止处处显示出香椿树街地带所罕见的大家
闺秀凤范。
学校后面的那座青砖小楼现在作了教师的宿舍。住宿舍的除了新来的倪老师,还有军属
袁老师和她的五岁的小女孩。小楼是西洋式的砖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凉台,凉台恰恰被楼
前高大的悬铃木树的枝叶所覆盖,透过绿色的枝叶可以看见整个简陋的校园,灰土操场,两
排用碎砖残瓦垒砌的教室,还有那座被改称为礼堂的从前教士布道做礼拜的礼拜堂。倪老师
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凉台,最初几天袁老师发现她每天早晨都站在凉台上,梳头,洗
漱,更多的时候是在读一本封皮磨损了的外国小说。
两位女教师第一次交谈虽然内容普通,属于必要的寒暄,但袁老师仍然对倪老师的一些
出乎意料的回答将信将疑。
你今年不到二十岁吧?
哪里,我都快满三十了。
袁老师不相信这个年龄,但对方的微笑看上去是诚实的善意的。
他们说你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可我听你说话倒像是北方人?
我从小死了父母,寄养在亲戚家里,我在天津长大,后来又去上海念书,连我自己也弄
不清我说话是什么口音了。
你在上海念的什么学校?是女子师范吗?
是的,我念的学校没有名气,只念了两年,后来生了一场病就辍学了。
袁老师察觉到对方脸上渐渐有一种不悦之色,于是谈话就戛然中止了。两个女教师站在
绿叶掩映的凉台上,起先挨得很近,慢慢地就分开了。沉默了一会儿,倪老师突然指着楼下
的一丛紫荆说,那丛紫荆挺好看的,我最喜欢紫荆花了,袁老师漫不经心地扫过倪老师手指
的方向,目光停留在前面的灰土操场上,袁老师重新朝倪老师身边靠近了一些,然后她用一
种紧张不安的语调说,你知道吗?操场上有狐狸出没,前天夜里我看见一只狐狸,一只雪白
的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倪教师教音乐课,也教美术课。她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也在侧耳
倾听。他们觉得她唱歌的方法很特别,懒洋洋的但却很动听,年纪大一些的则回忆着从前在
哪里听到过这样的歌谣,一个白发苍苍的女教师不屑地说,有什么好听的?是旧社会歌舞厅
里歌女的那一套。
趁倪教师不在办公室之际,教师们开始谈论她的来历。袁老师不失时机地对这个新同事
提出了各种疑惑,包括年龄、学历和籍贯各方面。我觉得她说话躲躲闪闪的,好像心里藏了
什么鬼。袁老师说,她每天都在凉台上洗头发,夜里也洗,昨天夜里我听见凉台上有泼水
声,跑出去一看,又是她在那里洗头,黑漆漆的披散着长发,穿了件白裙,像个女鬼,倒把
我吓了一跳。我问她怎么天天洗头,你们猜她怎么说?她说我不能把头上的粉笔灰留到明
天,我喜欢每天都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
她这么爱干净?一个教师说。
这么爱干净也是正常的,人家还是个姑娘。另一个教师说。
可是她不像个当教师的人,越看越不像,袁老师的神情显得很迷茫,她注意到同事们都
在等着她的下文,但她突然噤口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袁老师噗哧笑了笑,她说,我每次给学
生讲问号的使用时,脑子里就浮现出倪老师的脸,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两个女老师的宿舍仅隔着一道薄墙,那些夜晚袁老师时刻倾听着墙壁另一侧的动静,直
至沉沉的睡意袭来。除了小楼下杂草丛中夜虫的鸣唱和远处夜行火车的汽笛声,袁老师什么
也没听见,学校的秋夜异常宁静,两个单身女教师的夜晚也同样地清淡如水。
袁老师后来终于听见了来自隔壁宿舍的那一声夜半惊叫,倪老师的惊叫声并不尖利,但
听来非常恐怖。袁老师记得她奔出去敲倪老师的门时只穿着内衣,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
等着倪老师来开门,但门仍然紧闭着,房间里无人应答,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很疑惑。
她蹲下来寻找门上的一条缝隙,希望透过门缝发现里面的异常情况。但她很快发现那条缝被
一张牛皮纸从里面贴住了,纸上映着一点黯淡的昏黄的灯光,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是什么时
候把门缝封贴住的。
倪老师你到底怎么啦?袁老师的声音已经由焦灼变为沮丧,而且她身上单薄的内衣无法
抵御秋夜的凉意。倪老师的宿舍里却依然一片死寂,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袁老师开始怀疑
听见的惊叫是否幻觉,也抱着自己的双肩在倪老师的门前踯躅了一圈,这时候她清晰地听见
门后拉动灯绳关灯的声音,然后床板嘎吱响了一下,倪老师大概上床睡觉了。
无论如何这是件怪事,袁老师一夜未眠,猜测着那声惊叫和倪老师拒绝开门的原因,她
无法排遣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倪老师是一个谜,这个新来的女教师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站在凉台上刷牙,她的气色看上去与往日一样姣好清朗,
即使是唇下的牙膏沫也没有掩盖她的美丽。袁老师端着女儿的便盆冷眼观望着倪老师,心里
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倪老师你昨天夜里怎么啦?
怎么啦?倪老师侧首朝袁老师笑了笑,她朝凉台下吐了一口水说,昨天夜里我怎么啦?
我听见你惊叫,够吓人的。
我惊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叫了,可我跑过去你却不肯给我开门,昨天夜里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昨天夜里我看见了狐狸,就是你说的那只狐狸,白色的小小的狐狸,它
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你真看见了狐狸?袁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诧的表情,她心里清楚那天关于狐狸的话题
是一种即兴发挥,其实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操场上的白狐狸。
当然是真的,我站在窗边,看见那只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我不相信,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了,从来没有见过狐狸。袁老师说到这里意识到露了破
绽,于是又补上一句,我只是听别人说夜里操场上有狐狸出没。
倪老师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隐晦的冷冷的笑意,她随手将脸盆和杯子里的水朝楼下泼
去,这么说袁老师你在说谎,倪老师说,假如你是骗我的,那我也是骗骗你的,根本就没有
什么狐狸。
可是我听见你叫了,我拼命敲门你却没有开门。
我喜欢一个人,倪老师最后的回答听来意义含混,但她的敌意似乎是明显的。倪老师手
里的脸盆和脸盆里的杯子牙刷乒乒地碰撞着,她的脸现在是阴沉着的,这使她的容颜接近三
十岁而不是二十岁这个年龄。袁老师有点窘迫地看着她从身边疾速闪过。我是好意,我是怕
你有什么意外。袁老师朝倪老师的背影喊了一句,但倪老师似乎充耳未闻。
是一个薄雾袅袅的早晨,红旗小学简陋的校舍湮没在雾气和乌鸣声中,孩子们还没有上
学,这是一天中最宁静而抒情的时刻,但袁老师却无心欣赏小楼周围的秋日晨景,对于倪老
师的种种怀疑和猜度像一片乌云在她心里飘来荡去,这个奇怪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位教师的关系已经失去了所有温和或礼貌的色彩,不管是在小楼上还是在办公室里,
她们都是侧目而视,最让袁老师耿耿于怀的是倪老师的敌意居然殃及小孩子,袁老师三岁的
女孩摔在楼梯上嚎陶大哭时,倪老师从孩子身边绕过去,居然不肯伸手把孩子扶起来。袁老
师在办公室里向同事们多次谈及此事,我看她根本不是做教师的人,袁老师难以掩饰她的愤
怒和刻毒的情绪,她说,天知道她是干什么的,谁知道她的来历?谁知道她的出身?我看她
以前干什么事都像,就是不像学生,不像做教师的人。
办公室里的人对袁老师的话题似乎都很感兴趣,但是没有人附和她,他们更喜欢听而不
喜欢说。唯一作出反应的是红旗小学的校长老郑,老郑皱着眉头批评了袁老师,不要在背后
这样议论别人,影响同志间的团结,再说你对倪老师这样妄加猜测没有证据?
证据?袁老师冷笑一声,证据迟早会有的,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等着吧。
袁老师一直等待着的机会有一天似乎突然来临了,下午放学后她在搂上晾衣物,看见楼
下有三个中年男子朝上面张望,仅从他们西装革履的服饰打扮来看,袁老师就可以判断客人
来路不正。
你们找谁?袁老师一边高声询问一边抓紧了手里的叉杆。
倪香红住这里吗?楼下的男人操着典型的北方口音。
没胡倪香红只有倪红。袁老师话刚出口就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倪老师根本不叫倪红,
她是改过名字的。
这时侯倪老师已经来到凉台上,袁老师听见她边走边嘀咕着,谁找我?怎么会有人找
我?当倪老师扶住凉台的木栏杆朝下张望时,一边的袁老师发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脸色也变得苍白如纸,这使袁老师感到一份惊喜,她对身边的这个女人机械地重复着,有人
找你,有人来找你了。
倪老师没有说什么,倪老师提着她的灰丝绒裙子朝楼下飞跑,她很快和那三个陌生男人
站在一起了。他们在说着什么,袁老师很想听但什么也没有听清,她猜这是倪老师在搞鬼,
倪老师时刻提防着她的耳朵。
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没有上楼,倪老师领着那三个陌生男人穿过操场往学校外面走,袁老
师随即返回她的房间,打开了面对香椿树街的那扇西窗,西窗多年紧闭,插销已经锈死了,
袁老师费了很大劲才把窗子打开,她看见了秋风暮色中的香椿树街,街上的那些正在关门打
烊的小店铺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她看见倪老师和那三个陌生男人拐过街角:在织布厂的围墙
后面消失不见了。
袁老师在剩下的黄昏时分里心不在焉,她不知道倪老师带着三个男人去了哪里,但可以
确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倪老师回来得愈晚问题也就愈严重,袁老师这
样想着渐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管怎么说,她对倪老师来历的怀疑已经有了初步的证
明,她相信事情已经露出端倪了。
天色已经昏黑一片,倪老师仍然没有回来,袁老师抱着女儿在凉台上朝校门口观望了一
阵,看见的只是一片薄薄的幽暗和随风飘落的梧桐树叶,最后一个卖糖人的货郎正摇响泼浪
鼓从街上经过。袁老师突然感到隐隐的恐惧,她想倪老师会不会出事了?这种结果是她害怕
和不希望见到的。袁老师把女儿放到床上哄她睡觉,一边留心着外面楼梯上的动静。桌上的
闹钟指针指向九点的时候,她听见从楼梯上传来一阵迟滞拖沓的脚步声,袁老师冲到门外打
开了廊上的电灯,她看见倪老师站在她的宿舍门外,遍身寻找着她的钥匙。
你总算回来了。袁教师舒了口气搭讪道。
倪老师朝袁老师颔首一笑,她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苍白可怖,笑意是凄凉而柔和
的,袁老师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对方的这种微笑了。袁老师忍不住想追问那几个男人的身份,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而且倪老师很快发现她出门前忘了锁门,钥匙正插在挂锁上,于是倪
老师像平日一样取下挂锁,侧身进了她的宿舍。
怎么回事?袁老师独自在廊上站了会儿,想像着刚才倪老师离去的遭遇。没出事就好,
人回来就好,袁老师咕哝着关了灯回到她的宿舍,她想隔壁这个女人的一切快要水落石出
了,对于她的种种疑问也将会被确凿的证据所取代,现在袁老师心中有数,她觉得她应该上
床好好睡一觉了。
午夜时分倪老师的宿舍里再次传来一声悠长的惊叫,比上次更其尖厉和凄烈,隔壁的袁
老师和她的女孩一齐被惊醒了。袁老师听见板墙那侧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闯入了倪
老师的宿舍,袁老师抱起被吓哭了的女孩,睁大眼睛坐在黑暗中,她知道倪老师这次的夜半
惊叫是可怕的,而深夜的闯入者无疑是那三个陌生的操北方口音的男人、袁老师记得她听见
了倪老师的求援的叫声,袁老师帮帮我,快来帮帮我!但她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出去,一半出
于对那三个闯入者的恐惧,另一半也许出于对倪老师不友好态度的报复心理。袁老师甚至不
敢开灯,她用手捂住了女孩的嘴制止她的啼哭,因为她害怕灾祸殃及她和她的孩子。
隔壁的嘈杂声很快平息下来,倪老师的嘴似乎也被堵住了,凭脚步声可以判断他们把倪
老师弄下了楼。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怎么样了,最坏的估计是出了人命。后来袁老师跑到凉
台上,出于意料的是倪老师跟着三个男人走过操场,她好像没有受到伤害,在秋夜的月光下
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的丝绒裙子随风飘动,而且她的手里提看那口小巧的皮箱。袁老师没有想
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倪老师收拾了东西跟着那三个男人走了。
青砖小楼现在复归往日的寂静,但黑暗的空间里疑云密布,袁老师觉得倪老师如此不告
而别,证实了以前对她的种种怀疑都是正确的,她感到一丝欣慰,同时也对女邻居产生了一
种怜悯,不管怎么说,倪老师肯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夜凉如水,已经看不见黑暗中匆匆离开的那四条背影了,袁老师正要返回宿舍,这时候
她看见操场上有一团白影急驰而过,消失在礼堂的后面,月光照亮了那只动物的轮廓和皮
毛,袁老师看清那是只白狐狸,真的是一只小小的白色的狐狸,真的是传说中的那只狐狸。
郑校长从区上带回消息说,来无踪去无影的倪老师果然是个女骗子,她是从丈夫身边逃
出来的,而且她从前是在天津的妓院里被丈夫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能让她做人
民教师?郑校长满脸羞惭地说,我们都让她给骗了。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袁老师打断了郑校长的话茬,她在学生作业本上连续打了几个问
号,我第一眼看见她心里就有问号,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她像一只狐狸。
--------------
狐心深处
春天来了,小狐狸该娶亲了,从寒冷的冬天开始,小狐狸就已经坐在火炉旁用柔软的带着花香的草编结抬新娘的轿子了,终于森林里的冰雪融了,柳叶绿了,桃花开了,可以过山那边去迎亲了,小狐狸心里真高兴啊,走着走着他就忍不住抬着轿子跳起舞来,忽然他听到身后传来咚的一声,原来是狐狸新娘被摇下了座椅,小狐狸赶紧收起舞步,小心翼翼地走了回来……到家了,小狐狸请新娘子下轿,左请右请新娘子就是不出来,小狐狸只好自己掀开轿帘,可是看了一眼他就哭起来,原来一路上轿子中忽隐忽现的光芒是两颗装着萤火虫的月牙儿――那就是他认为是新娘子眼睛的东西;柔软金黄的狐衣则是一大蓬稻草――他还一直以为那是新娘子漂亮的尾巴呢――新娘子到哪里去了?小狐狸伤心地哭着,直哭到鼻涕都流出来,他刚想用衣袖去擦,眼前忽然多出一条雪白的手帕,他想也不想的接过来,可是慢着,这条手帕?小狐狸疑惑地转过头,然后他就看到他那似笑非笑的新娘子了,他大叫一声,也不管鼻涕有没有擦,就一把抱住了他的新娘子!
夏天的夜晚,是狐狸炼丹的时候,劳累了一天,大狐狸们都睡着了,小狐狸悄悄地从洞口探出头来,她们要到山上去炼丹,本来,狐妈妈们一再叮嘱她们炼丹要在洞里,千万不要跑到山上去招摇,否则仙丹会被坏心的动物们抢走吃掉,可是小狐狸们不管那些,她们叽叽喳喳地跑上山,争先恐后地从肚子里吐出仙丹,用力地抛向远空,呵!夏夜远山上的流焰就那样绽放了,此起彼伏的彩焰啊,起起落落地诉说着思念,远方的爱人啊,你可曾看见我为你修炼出来的爱的信念?
秋天的暴风雨夜,是小狐狸历劫的时候,虽然整个夏天,她们都在炼丹,希望能从那一片丹心中找到远方那个肯为她们遮风挡雨的人儿,可是,天下是那么的大,那人又是那么的远,谁知道到底找不找得到呢?于是她们拚命的修炼啊,五百年,一千年就这样过去了,她们找没找到呢?但愿她们找到!否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若她们仍未能托庇在那人的衣袂之下,一任狂虐的闪电直接击在身上,她们的灵魂会变成秋夜凄舞不停的流萤。
暴风雨过去了,冬天来临的时候,劫后余生的小狐狸挤在一起冬眠了,她们得在这个漫长寒冷的冬天做一个温暖而美丽的梦,在那个梦里,她们处身一个静谧温暖的宫殿,四周是一片黑暗,终于有一天,黑暗过去了,她看到的第一线天光却刺痛了她的眼,她难过地哭了起来,接着她发现那哭声不是她原来的声音,呱呱的,有点象青蛙,当然更象……她吃惊地睁大眼睛,她看到了一张憔悴但满足的笑脸,那张笑脸上有一双充满慈怜的大眼睛,那双大眼睛里写满属于人类的爱……
……
这就是小时候外婆关于狐狸的故事,外婆的眼睛细细长长的,外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变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外婆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是一个小狐狸变来的,外婆说小孩子出生到世上是为了来找一个雷雨夜共同经历风雨的人……
小时候听过太多关于狐狸的故事,以致于长到现在还常常似真似幻地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只狐狸变来的。
那是前世吧,我是一只美丽的小狐,在一个雨天,一个闪电劈下来的时候,我曾托庇于你的衣袂之下,那时我的皮毛洁白光滑,我的眼睛温柔妩媚但充满惊慌,以致于你情不自禁地停下匆匆的脚步俯身把我抱在怀里,于是在那个雨天,我在你怀中得到了重生,我记得的就是这样。
所以今世,我来到你身边,当然现在我已经不再是狐狸,为了接近你,我忍痛割掉自己的尾巴,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小女人,这些是你不知道的。你知道的只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都会死心塌地不求回报地跟在你身边,心甘情愿为你付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但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你只知道我妩媚、温柔、聪敏还有点狡猾,但你不怕我,因为你知道我爱你,但你常常为我的顽皮头痛,因为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露出我的刁蛮本色捉弄捉弄你,但是不要紧,我的分寸只会让你头痛而不会让你心痛――为什么不?我爱你,但爱是如此有趣的游戏,唉。
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生日,却又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一大束狗尾巴草,替你把衣服洗干净,却又在上面偷偷地印上口红,亲爱的,现在你明白了吧。明白每日清晨那句神秘的祝福是谁送给你的,每日黄昏缱绻的柔情是谁的思念,是我,哦不!不是我,是不知道多少年前那只雨夜在你的怀中得到永生的小狐狸……
今天又下雨了,我微笑着想,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但是现在我还没找到你呢,我只是坐在我的房间里,在写一篇名叫《狐心深处》的文章,但是今天真的下雨了,那时我出去晒太阳,就在暖暖的太阳照得我昏昏欲睡的时候,一个闪电劈下来,那时没有你的怀抱可供躲避,我一手勉强举在头顶遮风挡雨,一手瑟瑟地提着长裙,苍惶走在漫无边际的雨雾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再有一个闪电劈下来,我会不会变成一只小狐,在无边的雨地里苍惶四顾?
如同小狐脆弱的生命不能在雷雨夜独生,必须寻找一个人的衣袂以作荫庇一样,在雨中,我亦想要一个人的怀抱来为我撑起我无遮拦的天空,可那时我还没找到你,那时打雷了,好响的雷,我苍惶回顾,还好,尾巴没有露出来:)
天气预报说,明天又要下雨了,你的那个人呢,找到了吗?
作者:苏童
从前香椿树街没有一所学校,人们后来常常提起的红旗小学是由废弃的教堂改建的,那
时候来自异域的传教士早已远离这条世俗的没有信仰的街区,教堂附近杂草丛生,酿酒厂的
残渣垃圾被随意地堆放在礼拜堂里,而传教士曾居住过的青砖小楼里住着酒厂的一群粗蛮的
外地民工,他们把楼梯和凉台弄得尿迹斑斑污秽不堪,红旗小学来之不易,那些创业时期的
老教师后来习惯于对新来的教师回忆当初艰苦办学的情景,关于狐狸的故事也是那些白发教
师在课间休息时最喜欢的话题。
倪老师初到学校就很引人注目,她是被红旗小学的第一任校长郑老师领进简陋的办公室
的。人们记得她梳两条长辫,辫梢上扎一对豆绿色的蝴蝶结,她的裙子和随身带来的皮箱也
同样是雅致耐看的豆绿色的。办公室里的教师们都立刻注意到了倪老师的美丽,不仅由于她
的天生丽质和脉脉含情的微笑,更由于她的谈吐举止处处显示出香椿树街地带所罕见的大家
闺秀凤范。
学校后面的那座青砖小楼现在作了教师的宿舍。住宿舍的除了新来的倪老师,还有军属
袁老师和她的五岁的小女孩。小楼是西洋式的砖木结构,有一个很大的凉台,凉台恰恰被楼
前高大的悬铃木树的枝叶所覆盖,透过绿色的枝叶可以看见整个简陋的校园,灰土操场,两
排用碎砖残瓦垒砌的教室,还有那座被改称为礼堂的从前教士布道做礼拜的礼拜堂。倪老师
似乎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凉台,最初几天袁老师发现她每天早晨都站在凉台上,梳头,洗
漱,更多的时候是在读一本封皮磨损了的外国小说。
两位女教师第一次交谈虽然内容普通,属于必要的寒暄,但袁老师仍然对倪老师的一些
出乎意料的回答将信将疑。
你今年不到二十岁吧?
哪里,我都快满三十了。
袁老师不相信这个年龄,但对方的微笑看上去是诚实的善意的。
他们说你是浙江人,我也是浙江人,可我听你说话倒像是北方人?
我从小死了父母,寄养在亲戚家里,我在天津长大,后来又去上海念书,连我自己也弄
不清我说话是什么口音了。
你在上海念的什么学校?是女子师范吗?
是的,我念的学校没有名气,只念了两年,后来生了一场病就辍学了。
袁老师察觉到对方脸上渐渐有一种不悦之色,于是谈话就戛然中止了。两个女教师站在
绿叶掩映的凉台上,起先挨得很近,慢慢地就分开了。沉默了一会儿,倪老师突然指着楼下
的一丛紫荆说,那丛紫荆挺好看的,我最喜欢紫荆花了,袁老师漫不经心地扫过倪老师手指
的方向,目光停留在前面的灰土操场上,袁老师重新朝倪老师身边靠近了一些,然后她用一
种紧张不安的语调说,你知道吗?操场上有狐狸出没,前天夜里我看见一只狐狸,一只雪白
的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倪教师教音乐课,也教美术课。她在教室里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也在侧耳
倾听。他们觉得她唱歌的方法很特别,懒洋洋的但却很动听,年纪大一些的则回忆着从前在
哪里听到过这样的歌谣,一个白发苍苍的女教师不屑地说,有什么好听的?是旧社会歌舞厅
里歌女的那一套。
趁倪教师不在办公室之际,教师们开始谈论她的来历。袁老师不失时机地对这个新同事
提出了各种疑惑,包括年龄、学历和籍贯各方面。我觉得她说话躲躲闪闪的,好像心里藏了
什么鬼。袁老师说,她每天都在凉台上洗头发,夜里也洗,昨天夜里我听见凉台上有泼水
声,跑出去一看,又是她在那里洗头,黑漆漆的披散着长发,穿了件白裙,像个女鬼,倒把
我吓了一跳。我问她怎么天天洗头,你们猜她怎么说?她说我不能把头上的粉笔灰留到明
天,我喜欢每天都干干净净地上床睡觉。
她这么爱干净?一个教师说。
这么爱干净也是正常的,人家还是个姑娘。另一个教师说。
可是她不像个当教师的人,越看越不像,袁老师的神情显得很迷茫,她注意到同事们都
在等着她的下文,但她突然噤口不语了。过了一会儿袁老师噗哧笑了笑,她说,我每次给学
生讲问号的使用时,脑子里就浮现出倪老师的脸,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两个女老师的宿舍仅隔着一道薄墙,那些夜晚袁老师时刻倾听着墙壁另一侧的动静,直
至沉沉的睡意袭来。除了小楼下杂草丛中夜虫的鸣唱和远处夜行火车的汽笛声,袁老师什么
也没听见,学校的秋夜异常宁静,两个单身女教师的夜晚也同样地清淡如水。
袁老师后来终于听见了来自隔壁宿舍的那一声夜半惊叫,倪老师的惊叫声并不尖利,但
听来非常恐怖。袁老师记得她奔出去敲倪老师的门时只穿着内衣,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
等着倪老师来开门,但门仍然紧闭着,房间里无人应答,倪老师你怎么啦?袁老师很疑惑。
她蹲下来寻找门上的一条缝隙,希望透过门缝发现里面的异常情况。但她很快发现那条缝被
一张牛皮纸从里面贴住了,纸上映着一点黯淡的昏黄的灯光,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是什么时
候把门缝封贴住的。
倪老师你到底怎么啦?袁老师的声音已经由焦灼变为沮丧,而且她身上单薄的内衣无法
抵御秋夜的凉意。倪老师的宿舍里却依然一片死寂,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袁老师开始怀疑
听见的惊叫是否幻觉,也抱着自己的双肩在倪老师的门前踯躅了一圈,这时候她清晰地听见
门后拉动灯绳关灯的声音,然后床板嘎吱响了一下,倪老师大概上床睡觉了。
无论如何这是件怪事,袁老师一夜未眠,猜测着那声惊叫和倪老师拒绝开门的原因,她
无法排遣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倪老师是一个谜,这个新来的女教师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站在凉台上刷牙,她的气色看上去与往日一样姣好清朗,
即使是唇下的牙膏沫也没有掩盖她的美丽。袁老师端着女儿的便盆冷眼观望着倪老师,心里
突然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倪老师你昨天夜里怎么啦?
怎么啦?倪老师侧首朝袁老师笑了笑,她朝凉台下吐了一口水说,昨天夜里我怎么啦?
我听见你惊叫,够吓人的。
我惊吓了?我怎么不记得了?
你叫了,可我跑过去你却不肯给我开门,昨天夜里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也没有。昨天夜里我看见了狐狸,就是你说的那只狐狸,白色的小小的狐狸,它
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你真看见了狐狸?袁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诧的表情,她心里清楚那天关于狐狸的话题
是一种即兴发挥,其实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操场上的白狐狸。
当然是真的,我站在窗边,看见那只狐狸从操场上跑过去了。
我不相信,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了,从来没有见过狐狸。袁老师说到这里意识到露了破
绽,于是又补上一句,我只是听别人说夜里操场上有狐狸出没。
倪老师的嘴角上浮现出一丝隐晦的冷冷的笑意,她随手将脸盆和杯子里的水朝楼下泼
去,这么说袁老师你在说谎,倪老师说,假如你是骗我的,那我也是骗骗你的,根本就没有
什么狐狸。
可是我听见你叫了,我拼命敲门你却没有开门。
我喜欢一个人,倪老师最后的回答听来意义含混,但她的敌意似乎是明显的。倪老师手
里的脸盆和脸盆里的杯子牙刷乒乒地碰撞着,她的脸现在是阴沉着的,这使她的容颜接近三
十岁而不是二十岁这个年龄。袁老师有点窘迫地看着她从身边疾速闪过。我是好意,我是怕
你有什么意外。袁老师朝倪老师的背影喊了一句,但倪老师似乎充耳未闻。
是一个薄雾袅袅的早晨,红旗小学简陋的校舍湮没在雾气和乌鸣声中,孩子们还没有上
学,这是一天中最宁静而抒情的时刻,但袁老师却无心欣赏小楼周围的秋日晨景,对于倪老
师的种种怀疑和猜度像一片乌云在她心里飘来荡去,这个奇怪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位教师的关系已经失去了所有温和或礼貌的色彩,不管是在小楼上还是在办公室里,
她们都是侧目而视,最让袁老师耿耿于怀的是倪老师的敌意居然殃及小孩子,袁老师三岁的
女孩摔在楼梯上嚎陶大哭时,倪老师从孩子身边绕过去,居然不肯伸手把孩子扶起来。袁老
师在办公室里向同事们多次谈及此事,我看她根本不是做教师的人,袁老师难以掩饰她的愤
怒和刻毒的情绪,她说,天知道她是干什么的,谁知道她的来历?谁知道她的出身?我看她
以前干什么事都像,就是不像学生,不像做教师的人。
办公室里的人对袁老师的话题似乎都很感兴趣,但是没有人附和她,他们更喜欢听而不
喜欢说。唯一作出反应的是红旗小学的校长老郑,老郑皱着眉头批评了袁老师,不要在背后
这样议论别人,影响同志间的团结,再说你对倪老师这样妄加猜测没有证据?
证据?袁老师冷笑一声,证据迟早会有的,我相信我的直觉你们等着吧。
袁老师一直等待着的机会有一天似乎突然来临了,下午放学后她在搂上晾衣物,看见楼
下有三个中年男子朝上面张望,仅从他们西装革履的服饰打扮来看,袁老师就可以判断客人
来路不正。
你们找谁?袁老师一边高声询问一边抓紧了手里的叉杆。
倪香红住这里吗?楼下的男人操着典型的北方口音。
没胡倪香红只有倪红。袁老师话刚出口就意识到一个新的问题,倪老师根本不叫倪红,
她是改过名字的。
这时侯倪老师已经来到凉台上,袁老师听见她边走边嘀咕着,谁找我?怎么会有人找
我?当倪老师扶住凉台的木栏杆朝下张望时,一边的袁老师发现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
脸色也变得苍白如纸,这使袁老师感到一份惊喜,她对身边的这个女人机械地重复着,有人
找你,有人来找你了。
倪老师没有说什么,倪老师提着她的灰丝绒裙子朝楼下飞跑,她很快和那三个陌生男人
站在一起了。他们在说着什么,袁老师很想听但什么也没有听清,她猜这是倪老师在搞鬼,
倪老师时刻提防着她的耳朵。
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没有上楼,倪老师领着那三个陌生男人穿过操场往学校外面走,袁老
师随即返回她的房间,打开了面对香椿树街的那扇西窗,西窗多年紧闭,插销已经锈死了,
袁老师费了很大劲才把窗子打开,她看见了秋风暮色中的香椿树街,街上的那些正在关门打
烊的小店铺和行色匆匆的路人,她看见倪老师和那三个陌生男人拐过街角:在织布厂的围墙
后面消失不见了。
袁老师在剩下的黄昏时分里心不在焉,她不知道倪老师带着三个男人去了哪里,但可以
确定他们之间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倪老师回来得愈晚问题也就愈严重,袁老师这
样想着渐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不管怎么说,她对倪老师来历的怀疑已经有了初步的证
明,她相信事情已经露出端倪了。
天色已经昏黑一片,倪老师仍然没有回来,袁老师抱着女儿在凉台上朝校门口观望了一
阵,看见的只是一片薄薄的幽暗和随风飘落的梧桐树叶,最后一个卖糖人的货郎正摇响泼浪
鼓从街上经过。袁老师突然感到隐隐的恐惧,她想倪老师会不会出事了?这种结果是她害怕
和不希望见到的。袁老师把女儿放到床上哄她睡觉,一边留心着外面楼梯上的动静。桌上的
闹钟指针指向九点的时候,她听见从楼梯上传来一阵迟滞拖沓的脚步声,袁老师冲到门外打
开了廊上的电灯,她看见倪老师站在她的宿舍门外,遍身寻找着她的钥匙。
你总算回来了。袁教师舒了口气搭讪道。
倪老师朝袁老师颔首一笑,她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苍白可怖,笑意是凄凉而柔和
的,袁老师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对方的这种微笑了。袁老师忍不住想追问那几个男人的身份,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了,而且倪老师很快发现她出门前忘了锁门,钥匙正插在挂锁上,于是倪
老师像平日一样取下挂锁,侧身进了她的宿舍。
怎么回事?袁老师独自在廊上站了会儿,想像着刚才倪老师离去的遭遇。没出事就好,
人回来就好,袁老师咕哝着关了灯回到她的宿舍,她想隔壁这个女人的一切快要水落石出
了,对于她的种种疑问也将会被确凿的证据所取代,现在袁老师心中有数,她觉得她应该上
床好好睡一觉了。
午夜时分倪老师的宿舍里再次传来一声悠长的惊叫,比上次更其尖厉和凄烈,隔壁的袁
老师和她的女孩一齐被惊醒了。袁老师听见板墙那侧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闯入了倪
老师的宿舍,袁老师抱起被吓哭了的女孩,睁大眼睛坐在黑暗中,她知道倪老师这次的夜半
惊叫是可怕的,而深夜的闯入者无疑是那三个陌生的操北方口音的男人、袁老师记得她听见
了倪老师的求援的叫声,袁老师帮帮我,快来帮帮我!但她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出去,一半出
于对那三个闯入者的恐惧,另一半也许出于对倪老师不友好态度的报复心理。袁老师甚至不
敢开灯,她用手捂住了女孩的嘴制止她的啼哭,因为她害怕灾祸殃及她和她的孩子。
隔壁的嘈杂声很快平息下来,倪老师的嘴似乎也被堵住了,凭脚步声可以判断他们把倪
老师弄下了楼。袁老师不知道倪老师怎么样了,最坏的估计是出了人命。后来袁老师跑到凉
台上,出于意料的是倪老师跟着三个男人走过操场,她好像没有受到伤害,在秋夜的月光下
袁老师看见倪老师的丝绒裙子随风飘动,而且她的手里提看那口小巧的皮箱。袁老师没有想
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倪老师收拾了东西跟着那三个男人走了。
青砖小楼现在复归往日的寂静,但黑暗的空间里疑云密布,袁老师觉得倪老师如此不告
而别,证实了以前对她的种种怀疑都是正确的,她感到一丝欣慰,同时也对女邻居产生了一
种怜悯,不管怎么说,倪老师肯定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夜凉如水,已经看不见黑暗中匆匆离开的那四条背影了,袁老师正要返回宿舍,这时候
她看见操场上有一团白影急驰而过,消失在礼堂的后面,月光照亮了那只动物的轮廓和皮
毛,袁老师看清那是只白狐狸,真的是一只小小的白色的狐狸,真的是传说中的那只狐狸。
郑校长从区上带回消息说,来无踪去无影的倪老师果然是个女骗子,她是从丈夫身边逃
出来的,而且她从前是在天津的妓院里被丈夫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女人,怎么能让她做人
民教师?郑校长满脸羞惭地说,我们都让她给骗了。
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袁老师打断了郑校长的话茬,她在学生作业本上连续打了几个问
号,我第一眼看见她心里就有问号,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她像一只狐狸。
--------------
狐心深处
春天来了,小狐狸该娶亲了,从寒冷的冬天开始,小狐狸就已经坐在火炉旁用柔软的带着花香的草编结抬新娘的轿子了,终于森林里的冰雪融了,柳叶绿了,桃花开了,可以过山那边去迎亲了,小狐狸心里真高兴啊,走着走着他就忍不住抬着轿子跳起舞来,忽然他听到身后传来咚的一声,原来是狐狸新娘被摇下了座椅,小狐狸赶紧收起舞步,小心翼翼地走了回来……到家了,小狐狸请新娘子下轿,左请右请新娘子就是不出来,小狐狸只好自己掀开轿帘,可是看了一眼他就哭起来,原来一路上轿子中忽隐忽现的光芒是两颗装着萤火虫的月牙儿――那就是他认为是新娘子眼睛的东西;柔软金黄的狐衣则是一大蓬稻草――他还一直以为那是新娘子漂亮的尾巴呢――新娘子到哪里去了?小狐狸伤心地哭着,直哭到鼻涕都流出来,他刚想用衣袖去擦,眼前忽然多出一条雪白的手帕,他想也不想的接过来,可是慢着,这条手帕?小狐狸疑惑地转过头,然后他就看到他那似笑非笑的新娘子了,他大叫一声,也不管鼻涕有没有擦,就一把抱住了他的新娘子!
夏天的夜晚,是狐狸炼丹的时候,劳累了一天,大狐狸们都睡着了,小狐狸悄悄地从洞口探出头来,她们要到山上去炼丹,本来,狐妈妈们一再叮嘱她们炼丹要在洞里,千万不要跑到山上去招摇,否则仙丹会被坏心的动物们抢走吃掉,可是小狐狸们不管那些,她们叽叽喳喳地跑上山,争先恐后地从肚子里吐出仙丹,用力地抛向远空,呵!夏夜远山上的流焰就那样绽放了,此起彼伏的彩焰啊,起起落落地诉说着思念,远方的爱人啊,你可曾看见我为你修炼出来的爱的信念?
秋天的暴风雨夜,是小狐狸历劫的时候,虽然整个夏天,她们都在炼丹,希望能从那一片丹心中找到远方那个肯为她们遮风挡雨的人儿,可是,天下是那么的大,那人又是那么的远,谁知道到底找不找得到呢?于是她们拚命的修炼啊,五百年,一千年就这样过去了,她们找没找到呢?但愿她们找到!否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若她们仍未能托庇在那人的衣袂之下,一任狂虐的闪电直接击在身上,她们的灵魂会变成秋夜凄舞不停的流萤。
暴风雨过去了,冬天来临的时候,劫后余生的小狐狸挤在一起冬眠了,她们得在这个漫长寒冷的冬天做一个温暖而美丽的梦,在那个梦里,她们处身一个静谧温暖的宫殿,四周是一片黑暗,终于有一天,黑暗过去了,她看到的第一线天光却刺痛了她的眼,她难过地哭了起来,接着她发现那哭声不是她原来的声音,呱呱的,有点象青蛙,当然更象……她吃惊地睁大眼睛,她看到了一张憔悴但满足的笑脸,那张笑脸上有一双充满慈怜的大眼睛,那双大眼睛里写满属于人类的爱……
……
这就是小时候外婆关于狐狸的故事,外婆的眼睛细细长长的,外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变成一条优美的弧线,外婆说每一个小孩子都是一个小狐狸变来的,外婆说小孩子出生到世上是为了来找一个雷雨夜共同经历风雨的人……
小时候听过太多关于狐狸的故事,以致于长到现在还常常似真似幻地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只狐狸变来的。
那是前世吧,我是一只美丽的小狐,在一个雨天,一个闪电劈下来的时候,我曾托庇于你的衣袂之下,那时我的皮毛洁白光滑,我的眼睛温柔妩媚但充满惊慌,以致于你情不自禁地停下匆匆的脚步俯身把我抱在怀里,于是在那个雨天,我在你怀中得到了重生,我记得的就是这样。
所以今世,我来到你身边,当然现在我已经不再是狐狸,为了接近你,我忍痛割掉自己的尾巴,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小女人,这些是你不知道的。你知道的只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都会死心塌地不求回报地跟在你身边,心甘情愿为你付出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但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你只知道我妩媚、温柔、聪敏还有点狡猾,但你不怕我,因为你知道我爱你,但你常常为我的顽皮头痛,因为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露出我的刁蛮本色捉弄捉弄你,但是不要紧,我的分寸只会让你头痛而不会让你心痛――为什么不?我爱你,但爱是如此有趣的游戏,唉。
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生日,却又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一大束狗尾巴草,替你把衣服洗干净,却又在上面偷偷地印上口红,亲爱的,现在你明白了吧。明白每日清晨那句神秘的祝福是谁送给你的,每日黄昏缱绻的柔情是谁的思念,是我,哦不!不是我,是不知道多少年前那只雨夜在你的怀中得到永生的小狐狸……
今天又下雨了,我微笑着想,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但是现在我还没找到你呢,我只是坐在我的房间里,在写一篇名叫《狐心深处》的文章,但是今天真的下雨了,那时我出去晒太阳,就在暖暖的太阳照得我昏昏欲睡的时候,一个闪电劈下来,那时没有你的怀抱可供躲避,我一手勉强举在头顶遮风挡雨,一手瑟瑟地提着长裙,苍惶走在漫无边际的雨雾里,我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再有一个闪电劈下来,我会不会变成一只小狐,在无边的雨地里苍惶四顾?
如同小狐脆弱的生命不能在雷雨夜独生,必须寻找一个人的衣袂以作荫庇一样,在雨中,我亦想要一个人的怀抱来为我撑起我无遮拦的天空,可那时我还没找到你,那时打雷了,好响的雷,我苍惶回顾,还好,尾巴没有露出来:)
天气预报说,明天又要下雨了,你的那个人呢,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