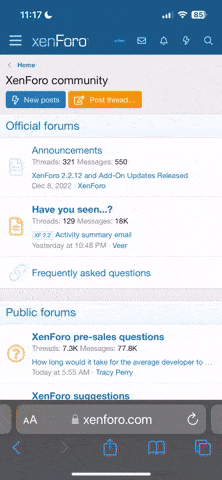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分享 山区的怀旧之行 (1人在浏览)
- 主题发起人 tianya
- 开始时间
我喜欢阅读真情流露的文学作品,那样,你能透过文字认识作者,是那么的真实。感谢陈贞老师的推荐。向喜欢文学的读者推荐陈淑芬写的袂花江,我只见过陈淑芬一次,因为她是个有社会地位的女士,所以我不好意思跟她主动打招呼,倒是她对我表示了友好之意,我觉得她平易近人。我很爱读她写的这篇文章,文章散发出的乡土气息太浓厚了……
[FONT=微软雅黑] 感 恩 袂 花 江[/FONT]
[FONT=楷体]作者 陈淑芬[/FONT]
袂花江,这诗一样的名字,画一样的美丽,一直以来,我为她自豪和骄傲。
袂花江是鉴江的第二大支流,发源于电白鹅凰嶂南坡。波澜壮阔的袂花江,以鹅凰嶂青鹅顶大山为起点,蜿蜒奔腾了100多公里,流域面积2516平方公里,于吴川兰石瓦窑口与梅江汇合流入鉴江后,奔向遥远的大海——南海。浩浩荡荡、川流不息的袂花江,以她那宽广博大的胸怀,哺育着两岸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过着恬静快乐的生活。袂花江两岸风景秀丽,生机盎然,四季如春。
我出生于袂花江畔。那里的一水一木,一沙一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当一些领导和同事得知我是袂花江畔长大的,都昵称我叫“袂花姑娘”,我心里也乐得美滋滋的。
袂花江畔那肥沃的土地,绿油油的庄稼,靠的是袂花江水源源不断的灌溉和滋润。我们的祖祖辈辈才得以在这里繁衍生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淡忙碌的生活。我的父亲和其他村民一样,除参加当时的集体劳动外,都利用早出晚归时间,在江边的滩涂坡地,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种菜,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充。大哥带着我经常到那里去帮忙浇水、除草、施肥。记得蔬菜种得不少,种类也很多,有豆角、绿豆、萝卜、芥菜、椰菜、通菜之类。靠近水边的那块地还种过慈菇、莲藕,长势很好,过年时才开挖。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看着那一个个圆溜溜的慈菇,胖嘟嘟的莲藕,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孩童时期那弯弯曲曲的袂花江岸上,长满了竹子,还有台湾相思树、苦楝树、凤凰树、榕树和水翁树等。我家离江边不到一百米,江边那一片茂密的竹林和树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和小伙伴们经常去那里掏鸟窝,捡竹虫。当看到哪根又嫩又高的竹笋顶端有虫蛀过的痕迹时,就用力抓住这根竹子使劲地摇,被虫蛀过的这截竹尾巴就会“噗嚓“一声掉下地来。当捡起来时里面肯定会有一至二条白胖胖正在一卷一缩蠕动着的竹笋虫。这时,只要往虫里挤进一粒盐,然后放进火炭里一烤,那就是香喷喷、美味十足、营养丰富的食品了。此外,我还经常背着萝筐,到那里去拾落叶和树枝给家里当柴烧,那是十分迷人的地方。
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夏天来临,晨曦初绽,鸟语蝉鸣时节,到那片树林里去捡蝉壳。这些蝉都是夜里从树根的土壤里爬上来的,爬到离地面约一尺高时,慢慢地把一身金黄色的壳脱下挂在树上,而它却在人们未留意时飞走了。每当雨后的夜晚,爬到树上脱壳的蝉就更多了。听母亲说,这些蝉壳可作药用,当地收购站设专柜予以收购。在母亲的鼓励下,每年那个时候,我都早早地爬起床,一个人悄悄地到那里去捡蝉壳。一年下来,也有一、二元钱的收入。这也许是我充满憧憬和遐想的童年时代最早为家里所作的贡献吧!我妈用这些钱为我添新衣服。
袂花江水清碧绿,波光粼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一直这样默默地流淌着,是那么安祥,那么迷人。春天时节,江边嫩绿嫩绿的青草猛长,这正是鸭、鹅、牛群理想的家园。于是,我们一边在那里放牧,一边嬉戏着,玩着孩童时期的游戏,唱着老掉牙的山歌。渴了,用双手捧起江水喝几口,累了就地躺在软绵绵的江边草坡上,望着蓝天、白云,望着自由飞翔的小鸟,遐想着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天上人间有趣的故事。到了夏天,热了,光溜溜地一头扎进水里,有时打水仗,有时比赛着看谁在水下憋的时间最长。袂花江多么令人向往,令人陶醉啊!
离我们村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江,这条江属袂花江的支流。我们村较固定的经常到那里去挑水、洗衣、洗澡的码头正对着这条江的入水口。由于这条江水面不宽,只有十几米左右,水也不深,而且清澈碧绿,经常可看到成群结队的鱼虾在水草中穿梭往来,除了有大人小孩会在那里捕鱼外,最惬意的事情是站在码头观看对岸钓鱼鹰抓鱼了。由于对岸的水翁树长得茂密挺拔,水翁树树枝一直伸展到了水面,机警、灵巧、勇敢、全神贯注的钓鱼鹰就站在那里,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水面。当听到“扑通”一声时,小鱼早已成了鱼鹰的囊中之物了。在江边看鸬鹚捕鱼,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从挑水码头再往前走十几米,是一片银白色的河滩,经常会有几条渔船停泊在那里。船上养着鸬鹚。这些鸬鹚是渔夫们捕鱼的得力助手。只见渔夫把竹杆往鸬鹚脚上一放,它就会乖乖地爬上竹杆,任由渔夫把它托起放到竹排上,然后渔夫撑着竹排,带着鸬鹚和鱼篓往水深的地方疾驰而去。到达目的地后,渔夫先在这条小江的两头把网下好,然后用竹杆大力拍打着水面,激起了一泼泼的水花。还用力踏着竹排,撞击水面发出“啪啪啪”的响声,这样是为了让鱼自投罗网吧。在做完这些功夫后,只听见渔夫“哟嘿”地叫了一声,站在竹排上的十几只鸬鹚像离弦之箭迅速地跃入水中。不多时,一个个又从水里冒了出来。渔夫们可乐了,一手抓住鸬鹚的脖子,一手从鸬鹚嘴里把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鲜鱼往鱼篓里放,最后再收网。这时,渔夫们可以鸣金收兵“满载而归”了。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们几个小伙伴想看看他们是怎样处理这些“战利品”的。于是我们沿着江边一路小跑,跟着渔夫又回到沙滩的渔船上。只见他们先把鱼分类,大条的鱼拿出去卖,小点的自己吃。有意思的是他们吃鱼是不用煎的,而是一锅煮,熟后放些盐油调味即可食用。当一掀开锅盖,那浓浓的鲜美的鱼香扑鼻而来时,直把我们这帮小朋友馋得直流口水。几十年过去了,当时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美丽富饶的袂花江,她那广阔的胸怀,坦坦荡荡,时刻拥抱和关爱着甘于奉献的人们。小时候,家里生活很拮据,如何解决我们兄妹的读书费用呢?我母亲想到了一个弄钱的办法,就是靠自己的体力到袂花江里去掏蚬卖钱。即用小铁棒做成一个长约一尺,宽约六寸左右的长方形网状蚬耙,再用一条二、三米长的竹杆固定平衡好。使用时,用两只手紧握着竹杆,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拉,直到感觉网筛很重了,才停下来。网筛里装的既有蚬,但更多的是沙、石、瓦块和木梢之类的东西。这时,就要用力地在水中摇动着网筛,使沙、石、木梢去掉,然后再轻轻地借着水力反复淘洗。由于蚬比沙石轻,只要反复地用水淘洗几次,蚬和沙石就分开了。这时就可以把蚬倒进早已准备好的木桶(用一条绳子把木桶固定后拴在腰上)里。就这样,我母亲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一有时间就往江里跑,遇上农忙或生产队有活干时,还得先忙完集体活,待收工后才去。我母亲很能吃苦,只要生产队不开工,在水里一泡就是一整天。有时待生产队收工后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她也顾不上歇一歇,肩上扛着蚬耙,手里拿着木桶就往江里赶。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长年累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风里来,雨里去。浅水的地方掏遍了,蚬越来越少了,就往水深的地方去掏,附近这一带掏过了,就到较远的地方去掏。上至袂花江的车头仔,下至鳌头的文运,都遍布了我母亲掏蚬的足迹,我母亲成了远近闻名的“掏蚬娘”。当时江上偶尔也见到有掏蚬的,但他们只是为了尝鲜,当菜吃,而像我母亲那样把它当作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去拼搏的就不多了。
掏蚬时,午餐一般是母亲出发时就备好带上,直到傍晚我和姐姐放学后,才依据母亲交待的方向一路沿江寻找她的踪影。当我们找到她时,夜幕已经降临,但她还泡在没过胸口的水里埋头苦干。这时,我们会凭着直觉对着河里那个影子“阿婶、阿婶”(我们称母亲为阿婶)地大声喊叫。当我们确认是母亲的声音了,就连忙在附近寻找母亲原先存放蚬的地方。母亲从江里掏上来的蚬还是“粗放型”的,还有三分之一是小石仔或别的东西。于是我和姐姐的任务就是对这些蚬进行第二次精选,即坐在水里用谷插将这些蚬再掏一次,还要用力搓干净沾在蚬身上的分泌物、脏东西,确认干净了,才能装上箩筐带回家。这时,天已经全黑了,母亲挑着起码有100多斤重的蚬走在前面,我和姐姐扛着蚬耙一脚深一脚浅地跟在后面。遇上有月亮时会好走些,如遇上没月亮或风雨天气,又没有手电筒,而且肚子早已饿得呱呱叫,还要走十几里的路,那种艰辛就可想而知了。听母亲说,有一次在九扇车那里,差点被江水冲走了。由于那里水流湍急,一脚踩空后被卷入了漩涡。在危急关头,母亲急中生智,立即把拴在腰上的半桶蚬倒掉,双手紧紧抱着木桶漂流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得以自救。
把蚬挑回家后,第二天,我母亲和父亲还得早早地起来,用一个大铁锅分批把蚬煮熟,把蚬肉取出用水清洗干净后,才让父亲拿到圩镇去卖。如遇上生产队有农活,还得等忙完后才拿出去卖,我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靠着父母的艰苦努力,我们几兄妹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还成为我们村里最有文化的文化人呢!
美丽富饶的袂花江,用她那洁白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千千万万像我母亲那样勤劳、勇敢、智慧、坚强的人们。我沐浴着袂花江的芬芳、雨露一天天长大了,又一步步远离了她……这些经历磨难是我人生一笔丰厚的财富,我一生一世感恩袂花江,感恩我伟大的母亲!
浏览附件330777
作者
相似主题
正在浏览此帖子的用户
当前在线: 2 (会员: 0, 游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