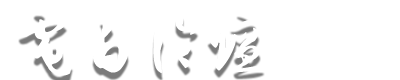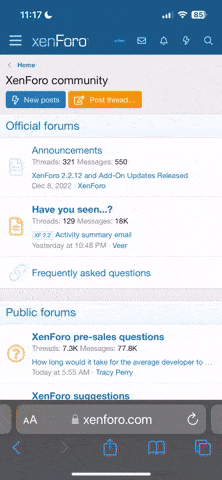近年来,我乐于看到中国的崛起,但更关心未来中国的何去何从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回报它的人民。因此我对ZG新领导人的上台就任,也就充满了期待。我期待中国的官学商精英能在未来的20年里,为中国做一番改头换面的大改革,不但造福人民,也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已放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民主改革上。如同人们所知道的,16及17世纪,欧洲仍处于落后的阶段。但18世纪起,从偏僻的苏格兰突然爆发式地发生了启蒙运动,迅速扩及英格兰和欧洲、美国,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社会政治改革,都是人类文明史未曾有过的创造性阶段。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就差不多是类似的挑战。
而对启蒙运动,我最推崇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他做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哲学系主任,这个位子在他之前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哈奇森都坐过。里德对这个时代貌似深奥的哲学不感兴趣,认为它对普遍的文明意义不大。因此他倡导一种常识哲学,它的前提是自然神学,认为无论人与自然都有不证自明的经验道理存在,人类本身就有真理之光,因此他主张人们要在不脱离经验下追求系统的科学知识,需以经验为前提,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哲学经验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它造成了第一次人类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他的道德人本主义则促成了个人主体意识的抬头。
美国开国元勋的那一代,拉什医生(Benjamin Rush)在爱丁堡大学留学,他就把常识哲学介绍给他的美国政论家朋友潘恩,并建议潘恩出书时以《常识》为名。这本《常识》对美国的独立建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常识哲学甚至也影响到杰斐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就把人的平等、公义概念等常识哲学的基本命题放了进去。杰斐逊后来成为第三任总统,他就根据常识来治国,他替美国规划的一套“制衡式民主”就很合乎常识。在政治上,以常识治国的意思就是重视人类需求公平正义的天性,并为这种天性设计出一套可长可久的制度。
人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官本位社会,官民在权利上不对等,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视贫富为个人的事而对人民权利疏于照顾,而官场上贪污腐化泛滥的原因。而随着时代的改革,中国人民的人的意识已经抬头,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将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用新的常识标准治国、建立制度、惩治贪腐、规划出照顾人民的福利安全体系,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划时代的大改革,绝不可能只靠官僚体系来完成,一定要靠着社会的多元制衡才可能落实。
我不主张西方式的民主,但我对媒体的自由和监督则寄予厚望。中国已需要根据常识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国家方案。邓小平时代,中国自主的力量不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了现在,中国已开始崛起,不能再走一步算一步,而是需有整套蓝图为腹案,大步地向未来前进。我最近看新兴国家的发展,无论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蒙古,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反贪及人民幸福的问题,如果中国以新的常识治国,发展出一套均富模式,不但其他新兴国家乐于效法,对西方社会也会有启发,这才是中国对世界做贡献。
也正因此,此刻的中国真正需要的乃是确定以常识治国之价值观。人类都有不证自明的正义感和要求公平对待的常识上的平等心,统治者就是要去满足人民的正义感和平等心。常识治国的话用中文来说,就是“以人民的心为自己的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有极多选项。但无论如何,分权与制衡这种常识行为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这也意味着此刻的中国在面临新的时代,无论反贪或消除贫富不均,一旦功成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历史开创啊!
近年来,我的学术兴趣已放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民主改革上。如同人们所知道的,16及17世纪,欧洲仍处于落后的阶段。但18世纪起,从偏僻的苏格兰突然爆发式地发生了启蒙运动,迅速扩及英格兰和欧洲、美国,18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社会政治改革,都是人类文明史未曾有过的创造性阶段。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就差不多是类似的挑战。
而对启蒙运动,我最推崇的不是别人,而是当时的道德哲学家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他做到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哲学系主任,这个位子在他之前亚当・斯密及其老师哈奇森都坐过。里德对这个时代貌似深奥的哲学不感兴趣,认为它对普遍的文明意义不大。因此他倡导一种常识哲学,它的前提是自然神学,认为无论人与自然都有不证自明的经验道理存在,人类本身就有真理之光,因此他主张人们要在不脱离经验下追求系统的科学知识,需以经验为前提,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一种最朴素的哲学经验主义和道德人本主义,它造成了第一次人类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他的道德人本主义则促成了个人主体意识的抬头。
美国开国元勋的那一代,拉什医生(Benjamin Rush)在爱丁堡大学留学,他就把常识哲学介绍给他的美国政论家朋友潘恩,并建议潘恩出书时以《常识》为名。这本《常识》对美国的独立建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的常识哲学甚至也影响到杰斐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就把人的平等、公义概念等常识哲学的基本命题放了进去。杰斐逊后来成为第三任总统,他就根据常识来治国,他替美国规划的一套“制衡式民主”就很合乎常识。在政治上,以常识治国的意思就是重视人类需求公平正义的天性,并为这种天性设计出一套可长可久的制度。
人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官本位社会,官民在权利上不对等,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视贫富为个人的事而对人民权利疏于照顾,而官场上贪污腐化泛滥的原因。而随着时代的改革,中国人民的人的意识已经抬头,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将走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用新的常识标准治国、建立制度、惩治贪腐、规划出照顾人民的福利安全体系,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划时代的大改革,绝不可能只靠官僚体系来完成,一定要靠着社会的多元制衡才可能落实。
我不主张西方式的民主,但我对媒体的自由和监督则寄予厚望。中国已需要根据常识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国家方案。邓小平时代,中国自主的力量不足,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到了现在,中国已开始崛起,不能再走一步算一步,而是需有整套蓝图为腹案,大步地向未来前进。我最近看新兴国家的发展,无论印度、菲律宾、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蒙古,几乎每个国家都出现了反贪及人民幸福的问题,如果中国以新的常识治国,发展出一套均富模式,不但其他新兴国家乐于效法,对西方社会也会有启发,这才是中国对世界做贡献。
也正因此,此刻的中国真正需要的乃是确定以常识治国之价值观。人类都有不证自明的正义感和要求公平对待的常识上的平等心,统治者就是要去满足人民的正义感和平等心。常识治国的话用中文来说,就是“以人民的心为自己的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有极多选项。但无论如何,分权与制衡这种常识行为乃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这也意味着此刻的中国在面临新的时代,无论反贪或消除贫富不均,一旦功成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历史开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