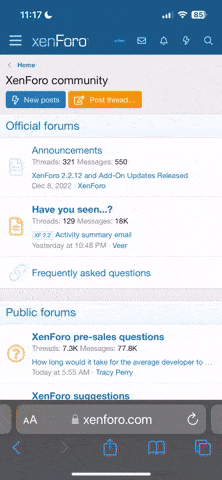老三是个卵
小学一年级
- 注册
- 2008-10-28
- 帖子
- 137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1
“如果我跟你老妈一块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前提是你只能救一个。”
小D说这句话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眼睛盯着手里的书,这是一本厚黑学,我正瞧得津津有味,心领神会。不大但明亮的房间里,CD里传来恬静的歌声,一帘阳光照在墙角的衣柜,小D正在整理我横七杂八的衣物。在这点上,她绝对是一位好姑娘,我相信谁要是取了这样的女人,确实是一件值得幸运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庸俗的社会里,找到一个贤妻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我抬起头看着她,我说那你希望我救谁。这样的问题我看过不下N次,任何一种回答都不会让人满意。我不是一个傻瓜,不会智商低到去回答女人这样的问题,那只能纠缠不清,没个了结。在这样问题上面,我完全相信女人是一条筋动物,只懂得咬住一头,紧紧的,没完没了地使劲。
小D一边折叠衣服一边说,问你呢,说呀,说你会救谁。我把视线移向窗外的阳光,说,都救。小D停下手头上的活说,不是说了嘛,只能救一个。你到底有没在听我说话。我翻了一页书,说,有听呀,可是为什么只能救一个呢,我两个都救为什么不可以。小D走过来一把夺下我手里的书,说,不要敷衍我,你认真回答我。天地良心,我有哪点不认真,我他妈的不知道多认真了,我就连高考都没这么认真。我有点生气了,你有完没完。我的情绪在我的口气里充分挥发出去。但很明显,她开始较劲了,说我怎么拉,不是叫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你用得着这样吗!操,我伸手抢过她手里的书,视线再次移到上面。过了一会,小D的抽泣声就混在音乐声中钻进我耳朵,并且在其中取得主旋律的地位。这在我听来,就如一根针不停地刺在心脏上。我扔掉手里的书,不把她搞定,要想看书那是异想天开。我瞪着她,厉声说,你怎么拉,你想怎样。小D仰起她五官还算端正的小脸,浅浅的泪痕在她一抹之下就被腰斩了,我想怎样,我能怎样,你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我不乐意了,说我怎样了,我什么什么时候怎样了。
“我问你,你到底救谁?”
“不是告诉了你吗?还要我重复一遍?得,都救。”
“你就是这样。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的,你就是没有在意,你就是没有在意我,你从来就没有在意我。”
她的声音连着泪水鼻涕一起轰炸着我的神经。他妈的,这些都让我恶心。我厌恶地看着她,你他妈的吃错药了,像条疯狗。她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往下排泄水分。我知道,她是在用狗屁上帝赋予她天生的武器抗衡我,她想把我融化在她的泪水当中,她想把我变成她的奴隶,一个她拥有绝对支配权的玩偶,一个在她呼叫中摇头摆尾呵斥中垂头丧气的小狗。开玩笑,她这点小心眼能逃出我法眼吗?她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只会增加我对她的厌倦。她提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像没了复眼的苍蝇,胡乱瞎撞,胡搞一通,胡作非为。她白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我一个明确的唯一的答案,救你,并且在回答的时候要脱口而出,不暇思考,斩钉截铁,理所当然般。她妈的她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她误以为恋爱中的男人也像她一般。SHIT!“救你”这个答案的存在性是很小的,几乎是没有,她忽略了或者是漠视又或者是根本就不懂一个男人的心态,女朋友没了可以再找最好是天天都有不同品种,可老妈呢,没了就是没了,什么叫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她完全没这个概念,我终于懂得了小D这些年来的书是白读了。女人真他妈的奇怪,总喜欢自找麻烦自找苦吃。
如此的气氛实在是让人郁闷,再呆着特没意思。于是我爬起来把裤子扎好,汲着拖鞋往外跑,出了门一直向北走。从我住处约摸走一千米,就是一条大江,贯穿着这座都市。人们一边亲切地歌颂着“母亲河,你流淌着我们的血,我们爱你,伟大的母亲”一边往河里扔垃圾排放污染物质。我混杂在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谱中,漫无目的地沿着堤岸走,看着表面四平八稳实质暗含涡旋的江水,心里闪过一念头,就是把小D扔进去。这么一来我烦躁的心情似乎获得了一丝安抚。我沉醉着,沉醉在小D被扔进去的丑态,在浮浮沉沉中大喊救命,江水撕开她的小嘴,挤进咽喉,在她肚子安营扎寨。在把她捞上来之前,我会清楚明了地告诉她,不就是救你吗!
我的歹毒让我暗暗吃惊,但却未至于悔恨,甚至我还享受着其中的惬意,就如沐着晚上的月光。小D的行经明显是在刺激我的神经挑战我的忍受能力。她用一个傻B的问题让我产生把她扔下去的冲动。可这一切在这之前还是相安无事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泛滥的韩剧情节中描写的那样已经达到了我答应登门拜访她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有着共同的希冀,我们还用心描绘过美好、满足、幸福的将来。我许诺过会爱她一辈子,让她幸福。她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我的胸脯上,肌肤贴着我们共同酝酿的温暖,我们的心连心。我说我爱你时候她用她那性感的小嘴啄了我一下。
这些还历历在目,随口而出。只是如今我的心情却是天地之别。好好梳理一下这场恋爱,才发现我使用的多是甜言蜜语,她使用的则是身体动作。或许可以这般说,我用口水换来了她的亲昵。在今天的不愉快当中,原本我也可以这样,那将会避免现在的沉闷,也许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而是在我那张还留着我和小D的汗味的床上,我们或许正在上面大汗淋漓地演绎着人类最初的欲望,我们在结合着,她用她的柔软包含着我的坚挺,我们在所谓爱的大海里,用我们的内心演奏一曲只属于我们的乐章。我们就在那里自由地畅游、消闲、甚至挥霍。
华灯初上,我方沿着原来的路往回走。气氛不变,变的只是面孔,它总是很轻易就把自己给隐匿。走过一小广场时候,一位身材发胖脸上擦满劣质化妆用品打扮得花枝招展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那身衣服就是地摊货十几块钱一件便宜得很的小姐对我招手,先生,要爽一下吗?我停下脚步,盯着她的脸庞。她在娇笑着,一如她那身衣服般廉价,眉角处的皱纹挤破上面一层层粉底,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她身上的那股味道是颓废糜烂,与她背后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完全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仿佛与生俱来。见我盯着她,她笑得更欢了,似乎我口袋里的钞票转眼间就跟了她姓,先生,要不要爽一下,很划算的,只要五十块。操,当然合算,腰包轻了,精子少了,走路飘起了,你享受了。我说怎么个爽法。她用手捂住血色大嘴作小女人状说,哎哟,你真幽默,净开玩笑。他妈的,我开玩笑?我就不能开玩笑吗?不错,我就是开玩笑,老子还开不起吗?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让自己不开玩笑,这样推销自己的货色,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不折腾一下,不给自己找一点乐子,那我还是我吗?于是我继续跟她扯,五十块太贵了,能不能少点?她用眼角嘌了我一下,大概是觉得这样很性感很来电,殊不知在我看来,只会让我恶心,让我作呕。她用发爹的声音说,已经很便宜了。五十块,绝对物有超值,要不你看一下货?绝对值,她边说边伸手把上衣往上面拉。我的妈呀!我用看吗,这么大一件活宝就摆在我跟前,虽然我五百多度的近视,也没戴眼镜,但我只需稍微一扫,就彻底否定了。我紧捂着肚子摇手说,别别,别。我往后退,她紧跟着我,声音也大了起来,先生,要不四十块。我没有理她,撒开步子就跑,江风在我耳边吹起,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瞧着我,我清楚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妓女在这一带招揽生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就在刚才,不远处就零落地散开着五六个这样的女人,她们用心盯着走过的人,用她们职业的眼光去获取某些可以搭讪的契机。
“先生,三十块,不可以再少了。”仿佛一个临终的病人有气无力的最后遗言,在我耳边模糊了,我相信我已经离开她的视野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大概现在她把目光转向别的男人,或许已经搭讪上了,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我尽可能的去推测,并且在这推测当中不得不暗笑,我想我他妈的太不是个东西了。
到了楼下,往上看,属于我的那扇窗户黑呼呼的,在周围的灯光映衬中,带有点深不可测。我不能确定小D是否还留在这。我在想倘若她在的话那我进去之后又会如何?我们会继续之前的争执,或者是她已弄好我们的晚餐正等着我回来,或者还在生闷气?我只能猜测着,女人永远是个不可捉摸的动物,往往出户意料地干些你猜不着摸不透的事情。上楼梯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小D正和一个陌生男人搅和在我的大床上,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比我帅比我有钱比我瘦比我性功能强比我更善于对付女人比我还他妈的不要脸比我还不是个东西。我的兴奋随着楼梯级次的增加而成正比,原本只是一丝水末,但等到我上去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条大河,往着汪洋大海的目标逼近。我真的不是个东西,居然期待着发生这种事,我期待门匙在门孔里扭动的时候他们所具有的反应,是惊慌失措找地方钻还是若无其事毫无理会继续把性爱进行到底?无论怎样,在我踏进之前,我是激动的,为即将揭晓的所有猜测,这让我有轻微的紧张,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像个小偷一样,蹑手蹑脚。灯光亮起,什么也没有,我所期待的是一片清冷,不要说陌生男人,如果不是整整齐齐的衣物摆在那,我甚至一度怀疑小D是否在这里出现过。
桌上有一张纸,被压在双喜牌烟盒下,我拿起一看,小D梨花带雨的脸浮现在上面。从字迹的内容及笔势不难得知书写人的心情,不是难过、伤心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分明是绝望与坚决。这样的后果明显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从来就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口角在我心目中根本就是鸡毛蒜皮。从头至今,我还想不到她做出这个决定的缘由。女人果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物种!
睡梦中,被一电话吵醒,我一边拿过手机一边发誓以后绝对要关掉它才会周公。小李说你他妈的还在冬眠呀,太阳都晒到*上了,他边说边大笑,我用他好象差我几百万不还的口气说关你鸟事,这正是睡觉好时光,你傻B了,有事就说有屁就放。
“靠!你也不看现在几点,我吃过还拉了两次,你他妈的还在找周老爷。”
“操,不行吗!甭废话,干嘛呢?”
“呵呵,过来搓两圈。”
“得了,一会过去。”
“好,记得快点,等你,不见不散。”
娘的,他说“等你,不见不散”时候像足一娘们,我在心里坚定了他的祖先就是李连英这一想头。我揉揉眉心,脑袋里像是装上了一个沙包那么沉。昨晚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美眉,两人就像脱光了衣服般,赤裸裸的对着,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聊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跟她聊女人,她跟我聊男人。我说女人是虚伪的动物,她说男人不是东西,在众多话语中,性是我们最好的心得。那种舒畅的感觉让我们相见恨晚,颇有人生一知己之叹。在其中,我们取得了一致。我们给与对方的话语当中剔除了个别字眼,竟然没什么出入。那种感觉真他妈的好,一点也不亚于灵肉交济,跟武侠小说里所说的打通任督两脉然后奇经八脉相勾连一辙。她告诉我爱不是用来说的,而应该是做,在爱前面的动词只能是做也必须是做,不需要什么狗屁言语,哪怕是有点也是多余的。我说单纯为做而做才是最好的追求,因为那是最简单的方式,不会渗杂着功利权益,惟有简单才是最纯粹的。她还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她身体的重要部位,她告诉我哪里是她的敏感兴奋点,她跟多少个男人野合过,哪个哪个男人如何的了得让她高潮迭起一浪接着一浪哪个哪个男人是个废物让她心慌难受空虚。我们聊得难分难舍,在道了N+1次的白白之后相约晚上再聊之后才真的白白。
不可否认的是,我的情欲在她的言语当中一直都是高昂的,像个战意十足的角斗士。我坚信要是她在我身边,我一定会不计后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的坚挺插进她的柔软之中,那必定是一场十足过瘾高潮不断的做爱。躺到床上时,我的神经还缠在她的话语上,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风筝,被她言语的线牵引着。我亢奋的脑细胞在幻想着,满足的同时带着空虚与失落。我想起了小D,脑子里像播放幻灯片般过滤着我们纠缠在一起的情景,却不由得失望。我没有在其中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来证明我曾到达过那座高峰,我有的只是向着上面爬,一直都是在某个位置徘徊。
见到小李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的事情。在小李狗窝一般的房间里,还有他的女朋友小茹,另外一个女孩则是生面孔,印象中没见过的。小李是我大学同学,毕业之后自己折腾着弄点小生意,现在混的人模狗样,日子也滋润起来了。麻将早已摆好,我跟小李瞎掰了几句就各就各位,噼啪劈啪的就彻起长城。还不够两圈我就贡献了两条红牛,这让本来生活就手紧的月光一族的我心情黯淡。我用力砸了只二万出去,随手拿起台面上的香烟,抽出一根就点火。整个房间里早就乌烟瘴气,小茹跟林丽(这么会工夫,足够知道名字绰绰有余了)一边紧紧地捂住鼻子一边死盯着台面,可能怕是漏牌。至于小李,就数他手气最旺,比鸡公还要旺,所以他的心情无疑是最舒畅的,因此他的笑声最膨胀。他妈的,他当然兴奋,不但有钞票进帐,又不落下与小茹打情骂诮,可谓一举两得。再说他也抽上那么三两根,故他是没眼瞧我了,他现在眼里只有我口袋里的钞票,在他眼里,我或许就跟一条待宰的鱼没啥分别。
首先忍受不了的是小茹,说,你就不能少抽点吗?能饭吃?
我黑着脸说,他妈的,手气背,没劲,抽两口,提神。
林丽小嘴张开了,我受不了。
从我进来到现在,林丽的话不多,我们胡言乱语时,她更多的只是微笑。我看了她一眼,说,这有什么,打牌不抽烟那还算打牌吗?这光摸不抽是根本解决不了瘾的。
小子,什么光摸不抽,这里可是有小妹妹在,别说这些不雅言语。小李打了个西,说。
林丽的小脸顿时红了,我透过烟雾瞧着她,觉得她特有味,操,你想到哪去了,就你那龌龊的脑袋,整天像便衣一样,随时警戒着周围,一有风吹草动就暗喜终于有行动了,真不知道小茹怎么忍受得了呢,要我是小茹,早一脚把你给踢了。说完我就把目光转向小茹,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什么跟什么呀!关我什么事,你们不要扯到我身上来,坏东西。”
“哈,得,我们都是坏东西,你是好东西。”晕,我又摸到一张二万,没好气地说。
“碰!”小李再次发出噪音,“你别扯,谁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是什么德行呢。”
“我怎了。”
“切,装,你就装吧。咱们在学校那时候你是怎的,就不要我多说了吧。”
林丽瞧了我两眼,捂着嘴巴问小李:“你给说说,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我吞了一口烟,怪声怪气地说,老子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林丽看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说,那我就更想听听了。
我说,莫不成大姐对俺有性趣?
“去你的!”林丽从旁边伸过手来在我手背上捏了一下,这小妮子真是熟得够快,三言两语后就对我动手动脚了,就她那点劲,只能达到让我舒服一下而不会疼痛的地步。
小茹说,你别臭美了,以为自己是国宝。
“切,”我做了一个鄙视她的表情,“国宝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可是独一无二永远不会再有的品种,千万不要错过。”我说到后来已经是对着林丽,当然最后那句也是对她说的。
“少来,就你那德行,”小茹转过头对林丽说,“整一自恋狂在眼前。”
自恋狂没什么不好,没人恋就要自己恋,即使是有人恋也不如自己恋来得真实可靠。我承认我是个自恋狂,有什么关系?没关系!
小李也摸过一根烟,在小茹的责备目光下抽了一口,说,林丽你不知道,这家伙以前牛B得很。那次我们被辅导员训,只有他跟辅导员急,你知道他用什么来急吗?你一定猜不着,他妈的,我一直都服了他,他妈的他居然用大粪和性器官。
我说,那还不是小意思。我故作轻松,其实心里并不是这样,我只是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烦躁,尤其是在林丽难以捉摸的眼光中,小李子,你别乱搞我的清白,小心我告你诽谤。靠,老子现在什么都没,只剩清白,再说小心我跟你急。其实小李说的没错,我也曾一度很欣赏自己,只是现在,我却莫名其妙的要跟过去划清界限。
“糊了!”小李嘴角挑着烟,两手各握一边把牌给开了,他娘的手气那么好,又自摸。自摸让他完全忽略了我把他称之为小李子。我摸摸裤兜,说,今儿手气背,改天再玩。
“哇,不是吧,刚上瘾你就不来了。”小茹的反应最大,跟一个正闭着眼睛呻吟的女人等待着对方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却晓得对方已经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能不大吗?
我笑了起来,说,这剩下的瘾你找小李帮忙你解决,相信他是乐意之至。今儿我是不玩了。边说边往外走,等哪天手气顺了,再战三百回合,小心你们的内裤都输给我。
“还早呢,不玩就坐会,再不在这里吃完晚饭再走。”
“谢了,甭操心,怎好意思打搅你们二人世界。”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话影响,一直沉默的林丽屁股在离开了椅子,说,我也回去了。
我们一前一后在小李两口子数着我的钞票时候出来了。我双手分别插在裤兜里,走起路来一摆一晃,一幅吊儿郎当样。林丽在后面叫住我说你上哪去?我回头说,我能上哪去,随便溜达。你呢?她说她也不知道上哪,又还不想回去。她的目光盯着鞋尖。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的是一双淡绿的高跟凉鞋,她完美干净白质的小脚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有恋脚癖,尤其是对着女人的小脚特有感觉,那比艺术品还要艺术得很。有人说我变态,管他呢,在享受艺术品带给我舒适愉快的时候,我怎么有空去理会这些!
“要不咱们随便逛逛。”林丽察觉到了我的异态,用声音来“提醒”我。
“成,那咱们随便溜达溜达。”
就这样,我们一前一后相距三四米的距离就消失了。我在她的左边,她在我的右边。我们漫无目的地随着顺流逆流的人群。偶尔,我们的手臂会碰到一起,肌肤在摩擦。我发觉她似乎有点主动。这个发现让我心情愉快不少,怎么说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惹人烦的角色总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喜悦的分子在我们摩擦中诞生了,它从我们肌肤的毛孔中钻进来,在血液循环中一遍遍地带给我们一些微妙的体验。我们沉默着,似乎生怕一开口就会把这份微妙扼杀。没有人保证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真实,因此我们百般小心呵护着,一如照顾自家的孩子一般无微无至。呈现在我们前方的是不见底的路,我们的身影闪过一道道横向的岔口,向前走,至于哪里是停落点,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后来,回想起与林丽的相遇,除了曾经相伴着走过一段路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曾存在。对于她,留在我印象中的残影也就那么一点点。我只知道她叫林丽,其他的职业年龄喜好是否有男朋友有过几个男朋友老家在何处都有些什么人喜欢用哪个牌子的卫生棉是否对我产生爱意如此之类的都是一片空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她就象一颗在夜空中一擦而过的陨石,在我的摩擦中划下了一道美丽的亮光,成为我的流星。
我们在公园里完事之后,在我家的床上,她问我使用大粪和性器官来急的那码事。那些陈年往事,好象我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有一个屁眼,都从那里往外排泄,差别不同的是它的外形大小伸缩度和所排泄的物质形状质地稀稠浓度罢了,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同一码事。我那时候是想藉此来告诉那个辅导员,我们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大不了,不要在那里张牙舞爪。我大概地把这个告诉了林丽,至于性器官,我则没说,因为那时候她已经大笑着抓住了我的老二。林丽在床上跟平时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的目清眉秀青纯可人的外观彻底被抛弃。她热情似火,如喷发的火山,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身体,她的小嘴唇像个饿坏的孩子无休止地咬着我,想完全地把我吞掉。
早上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事,是关于台风的。里面称今年迄今为止最好风级的台风将会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在这座城市登陆。中午,老天果然拉下了脸,变得阴沉,风也刮起来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尘土甚嚣的天空,一起一落的是废纸残菜叶子,行人慌慌张张地闪过,向着各自的目的。整个原本有条有理的城市丢光了她的沉稳,慢慢混乱,然后空洞。一扇扇紧闭的窗户里,不知道是什么。
我妈给我挂了一电话,嘱咐我要小心台风。苍老的声音里是对我莫大的关切,在这混乱的慌张中,她的话就如一支镇定剂,让我糟糕的心情好起来。我先起了小D,想知道她怎样了,但终犹豫了。
像是印证这个时代科学的伟大与是实用性,台风如预报的那样准时降临鬼哭狼嚎的风夹带着豆子般大小的雨珠敲打在玻璃上,停电瞬间放眼之处皆是黑呼呼一片,恐惧划过我的心脏,我感到乏力,仿佛世界末日。
关于这篇文字,是时候告一段落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一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事情,都有一个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局。生活就像一篇记叙文。在这里,我想必须得说说小D,我们也曾联系过,在分手已成事实,我们的联系不是留恋与否。而对于分手的缘由则归罪于我心目中没有一点她的位置。小D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淡若开水,像是述说一件完全与她无关的事情,她有资格这样,她就快结婚了,新郎哥比我帅比我有钱比我瘦比我性功能强比我更善于对付女人,至于是否比我还他妈的不要脸比我还不是个东西,那我就不清楚了。
“或许你的心中有我的存在,只是我感觉不到,你所处的方式是我所明白不了的。”
我想起那天她留给我的话。告别时候,我们互相衷心祝福对方。或许生活着,我们所留恋的只是自己,一如恋爱,爱的往往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林丽,虽然我不只于一次在小李那里出现,但却从不在见她,她已经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我们只是偶然的相逢在一起,各自谋取自己的需要,我跟她就如寒冬里两具冰冷的身躯,缠和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取暖。我明白这个时候,已经是换了一分工作。早在和小D争吵之前我就厌倦了那个工作,这份厌倦散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与那晚的那位美眉说起这些时间发生的这一切,我说我终于体会到了站在高峰处的感受。她说你一直都是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之中。她还说,我们生存在这座钢铁森林中,早就缺乏了先天,我们苟活着,半死不活的。她最后告诉我,生活就如一座密室,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惟有想方设法去钻个孔,从孔里获取生活的腐败营养,继续苟活下去。
是的,的确如此,也应当这般。台风肆虐后,城市角落里到处闪烁着清洁工忙碌的身影,一张张操着各种各样的脸谱重新活跃在城市的城墙上。很快,又将焕然一新。走在街上,我忽然想起成为我跟小D争吵的导火线“你到底救谁?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往干净的道上吐了一口浓痰,他妈的,都救!
小D说这句话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眼睛盯着手里的书,这是一本厚黑学,我正瞧得津津有味,心领神会。不大但明亮的房间里,CD里传来恬静的歌声,一帘阳光照在墙角的衣柜,小D正在整理我横七杂八的衣物。在这点上,她绝对是一位好姑娘,我相信谁要是取了这样的女人,确实是一件值得幸运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庸俗的社会里,找到一个贤妻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我抬起头看着她,我说那你希望我救谁。这样的问题我看过不下N次,任何一种回答都不会让人满意。我不是一个傻瓜,不会智商低到去回答女人这样的问题,那只能纠缠不清,没个了结。在这样问题上面,我完全相信女人是一条筋动物,只懂得咬住一头,紧紧的,没完没了地使劲。
小D一边折叠衣服一边说,问你呢,说呀,说你会救谁。我把视线移向窗外的阳光,说,都救。小D停下手头上的活说,不是说了嘛,只能救一个。你到底有没在听我说话。我翻了一页书,说,有听呀,可是为什么只能救一个呢,我两个都救为什么不可以。小D走过来一把夺下我手里的书,说,不要敷衍我,你认真回答我。天地良心,我有哪点不认真,我他妈的不知道多认真了,我就连高考都没这么认真。我有点生气了,你有完没完。我的情绪在我的口气里充分挥发出去。但很明显,她开始较劲了,说我怎么拉,不是叫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而已,你用得着这样吗!操,我伸手抢过她手里的书,视线再次移到上面。过了一会,小D的抽泣声就混在音乐声中钻进我耳朵,并且在其中取得主旋律的地位。这在我听来,就如一根针不停地刺在心脏上。我扔掉手里的书,不把她搞定,要想看书那是异想天开。我瞪着她,厉声说,你怎么拉,你想怎样。小D仰起她五官还算端正的小脸,浅浅的泪痕在她一抹之下就被腰斩了,我想怎样,我能怎样,你什么时候都是这样。我不乐意了,说我怎样了,我什么什么时候怎样了。
“我问你,你到底救谁?”
“不是告诉了你吗?还要我重复一遍?得,都救。”
“你就是这样。你到底有没有在意我的,你就是没有在意,你就是没有在意我,你从来就没有在意我。”
她的声音连着泪水鼻涕一起轰炸着我的神经。他妈的,这些都让我恶心。我厌恶地看着她,你他妈的吃错药了,像条疯狗。她没有说话,只是一味往下排泄水分。我知道,她是在用狗屁上帝赋予她天生的武器抗衡我,她想把我融化在她的泪水当中,她想把我变成她的奴隶,一个她拥有绝对支配权的玩偶,一个在她呼叫中摇头摆尾呵斥中垂头丧气的小狗。开玩笑,她这点小心眼能逃出我法眼吗?她这样做只能适得其反,只会增加我对她的厌倦。她提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盲目的。像没了复眼的苍蝇,胡乱瞎撞,胡搞一通,胡作非为。她白痴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我一个明确的唯一的答案,救你,并且在回答的时候要脱口而出,不暇思考,斩钉截铁,理所当然般。她妈的她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她误以为恋爱中的男人也像她一般。SHIT!“救你”这个答案的存在性是很小的,几乎是没有,她忽略了或者是漠视又或者是根本就不懂一个男人的心态,女朋友没了可以再找最好是天天都有不同品种,可老妈呢,没了就是没了,什么叫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她完全没这个概念,我终于懂得了小D这些年来的书是白读了。女人真他妈的奇怪,总喜欢自找麻烦自找苦吃。
如此的气氛实在是让人郁闷,再呆着特没意思。于是我爬起来把裤子扎好,汲着拖鞋往外跑,出了门一直向北走。从我住处约摸走一千米,就是一条大江,贯穿着这座都市。人们一边亲切地歌颂着“母亲河,你流淌着我们的血,我们爱你,伟大的母亲”一边往河里扔垃圾排放污染物质。我混杂在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谱中,漫无目的地沿着堤岸走,看着表面四平八稳实质暗含涡旋的江水,心里闪过一念头,就是把小D扔进去。这么一来我烦躁的心情似乎获得了一丝安抚。我沉醉着,沉醉在小D被扔进去的丑态,在浮浮沉沉中大喊救命,江水撕开她的小嘴,挤进咽喉,在她肚子安营扎寨。在把她捞上来之前,我会清楚明了地告诉她,不就是救你吗!
我的歹毒让我暗暗吃惊,但却未至于悔恨,甚至我还享受着其中的惬意,就如沐着晚上的月光。小D的行经明显是在刺激我的神经挑战我的忍受能力。她用一个傻B的问题让我产生把她扔下去的冲动。可这一切在这之前还是相安无事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像泛滥的韩剧情节中描写的那样已经达到了我答应登门拜访她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有着共同的希冀,我们还用心描绘过美好、满足、幸福的将来。我许诺过会爱她一辈子,让她幸福。她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我的胸脯上,肌肤贴着我们共同酝酿的温暖,我们的心连心。我说我爱你时候她用她那性感的小嘴啄了我一下。
这些还历历在目,随口而出。只是如今我的心情却是天地之别。好好梳理一下这场恋爱,才发现我使用的多是甜言蜜语,她使用的则是身体动作。或许可以这般说,我用口水换来了她的亲昵。在今天的不愉快当中,原本我也可以这样,那将会避免现在的沉闷,也许我就不会出现在这里,而是在我那张还留着我和小D的汗味的床上,我们或许正在上面大汗淋漓地演绎着人类最初的欲望,我们在结合着,她用她的柔软包含着我的坚挺,我们在所谓爱的大海里,用我们的内心演奏一曲只属于我们的乐章。我们就在那里自由地畅游、消闲、甚至挥霍。
华灯初上,我方沿着原来的路往回走。气氛不变,变的只是面孔,它总是很轻易就把自己给隐匿。走过一小广场时候,一位身材发胖脸上擦满劣质化妆用品打扮得花枝招展其实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那身衣服就是地摊货十几块钱一件便宜得很的小姐对我招手,先生,要爽一下吗?我停下脚步,盯着她的脸庞。她在娇笑着,一如她那身衣服般廉价,眉角处的皱纹挤破上面一层层粉底,露出庐山真面目来,她身上的那股味道是颓废糜烂,与她背后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完全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仿佛与生俱来。见我盯着她,她笑得更欢了,似乎我口袋里的钞票转眼间就跟了她姓,先生,要不要爽一下,很划算的,只要五十块。操,当然合算,腰包轻了,精子少了,走路飘起了,你享受了。我说怎么个爽法。她用手捂住血色大嘴作小女人状说,哎哟,你真幽默,净开玩笑。他妈的,我开玩笑?我就不能开玩笑吗?不错,我就是开玩笑,老子还开不起吗?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让自己不开玩笑,这样推销自己的货色,在这样的心情中,我不折腾一下,不给自己找一点乐子,那我还是我吗?于是我继续跟她扯,五十块太贵了,能不能少点?她用眼角嘌了我一下,大概是觉得这样很性感很来电,殊不知在我看来,只会让我恶心,让我作呕。她用发爹的声音说,已经很便宜了。五十块,绝对物有超值,要不你看一下货?绝对值,她边说边伸手把上衣往上面拉。我的妈呀!我用看吗,这么大一件活宝就摆在我跟前,虽然我五百多度的近视,也没戴眼镜,但我只需稍微一扫,就彻底否定了。我紧捂着肚子摇手说,别别,别。我往后退,她紧跟着我,声音也大了起来,先生,要不四十块。我没有理她,撒开步子就跑,江风在我耳边吹起,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瞧着我,我清楚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妓女在这一带招揽生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就在刚才,不远处就零落地散开着五六个这样的女人,她们用心盯着走过的人,用她们职业的眼光去获取某些可以搭讪的契机。
“先生,三十块,不可以再少了。”仿佛一个临终的病人有气无力的最后遗言,在我耳边模糊了,我相信我已经离开她的视野了。我一边走一边想,大概现在她把目光转向别的男人,或许已经搭讪上了,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我尽可能的去推测,并且在这推测当中不得不暗笑,我想我他妈的太不是个东西了。
到了楼下,往上看,属于我的那扇窗户黑呼呼的,在周围的灯光映衬中,带有点深不可测。我不能确定小D是否还留在这。我在想倘若她在的话那我进去之后又会如何?我们会继续之前的争执,或者是她已弄好我们的晚餐正等着我回来,或者还在生闷气?我只能猜测着,女人永远是个不可捉摸的动物,往往出户意料地干些你猜不着摸不透的事情。上楼梯时候我忽然有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小D正和一个陌生男人搅和在我的大床上,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男人,比我帅比我有钱比我瘦比我性功能强比我更善于对付女人比我还他妈的不要脸比我还不是个东西。我的兴奋随着楼梯级次的增加而成正比,原本只是一丝水末,但等到我上去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条大河,往着汪洋大海的目标逼近。我真的不是个东西,居然期待着发生这种事,我期待门匙在门孔里扭动的时候他们所具有的反应,是惊慌失措找地方钻还是若无其事毫无理会继续把性爱进行到底?无论怎样,在我踏进之前,我是激动的,为即将揭晓的所有猜测,这让我有轻微的紧张,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像个小偷一样,蹑手蹑脚。灯光亮起,什么也没有,我所期待的是一片清冷,不要说陌生男人,如果不是整整齐齐的衣物摆在那,我甚至一度怀疑小D是否在这里出现过。
桌上有一张纸,被压在双喜牌烟盒下,我拿起一看,小D梨花带雨的脸浮现在上面。从字迹的内容及笔势不难得知书写人的心情,不是难过、伤心那么简单,在我看来,那分明是绝望与坚决。这样的后果明显在我的意料之外。我从来就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口角在我心目中根本就是鸡毛蒜皮。从头至今,我还想不到她做出这个决定的缘由。女人果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物种!
睡梦中,被一电话吵醒,我一边拿过手机一边发誓以后绝对要关掉它才会周公。小李说你他妈的还在冬眠呀,太阳都晒到*上了,他边说边大笑,我用他好象差我几百万不还的口气说关你鸟事,这正是睡觉好时光,你傻B了,有事就说有屁就放。
“靠!你也不看现在几点,我吃过还拉了两次,你他妈的还在找周老爷。”
“操,不行吗!甭废话,干嘛呢?”
“呵呵,过来搓两圈。”
“得了,一会过去。”
“好,记得快点,等你,不见不散。”
娘的,他说“等你,不见不散”时候像足一娘们,我在心里坚定了他的祖先就是李连英这一想头。我揉揉眉心,脑袋里像是装上了一个沙包那么沉。昨晚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美眉,两人就像脱光了衣服般,赤裸裸的对着,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聊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我跟她聊女人,她跟我聊男人。我说女人是虚伪的动物,她说男人不是东西,在众多话语中,性是我们最好的心得。那种舒畅的感觉让我们相见恨晚,颇有人生一知己之叹。在其中,我们取得了一致。我们给与对方的话语当中剔除了个别字眼,竟然没什么出入。那种感觉真他妈的好,一点也不亚于灵肉交济,跟武侠小说里所说的打通任督两脉然后奇经八脉相勾连一辙。她告诉我爱不是用来说的,而应该是做,在爱前面的动词只能是做也必须是做,不需要什么狗屁言语,哪怕是有点也是多余的。我说单纯为做而做才是最好的追求,因为那是最简单的方式,不会渗杂着功利权益,惟有简单才是最纯粹的。她还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她身体的重要部位,她告诉我哪里是她的敏感兴奋点,她跟多少个男人野合过,哪个哪个男人如何的了得让她高潮迭起一浪接着一浪哪个哪个男人是个废物让她心慌难受空虚。我们聊得难分难舍,在道了N+1次的白白之后相约晚上再聊之后才真的白白。
不可否认的是,我的情欲在她的言语当中一直都是高昂的,像个战意十足的角斗士。我坚信要是她在我身边,我一定会不计后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的坚挺插进她的柔软之中,那必定是一场十足过瘾高潮不断的做爱。躺到床上时,我的神经还缠在她的话语上,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风筝,被她言语的线牵引着。我亢奋的脑细胞在幻想着,满足的同时带着空虚与失落。我想起了小D,脑子里像播放幻灯片般过滤着我们纠缠在一起的情景,却不由得失望。我没有在其中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来证明我曾到达过那座高峰,我有的只是向着上面爬,一直都是在某个位置徘徊。
见到小李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的事情。在小李狗窝一般的房间里,还有他的女朋友小茹,另外一个女孩则是生面孔,印象中没见过的。小李是我大学同学,毕业之后自己折腾着弄点小生意,现在混的人模狗样,日子也滋润起来了。麻将早已摆好,我跟小李瞎掰了几句就各就各位,噼啪劈啪的就彻起长城。还不够两圈我就贡献了两条红牛,这让本来生活就手紧的月光一族的我心情黯淡。我用力砸了只二万出去,随手拿起台面上的香烟,抽出一根就点火。整个房间里早就乌烟瘴气,小茹跟林丽(这么会工夫,足够知道名字绰绰有余了)一边紧紧地捂住鼻子一边死盯着台面,可能怕是漏牌。至于小李,就数他手气最旺,比鸡公还要旺,所以他的心情无疑是最舒畅的,因此他的笑声最膨胀。他妈的,他当然兴奋,不但有钞票进帐,又不落下与小茹打情骂诮,可谓一举两得。再说他也抽上那么三两根,故他是没眼瞧我了,他现在眼里只有我口袋里的钞票,在他眼里,我或许就跟一条待宰的鱼没啥分别。
首先忍受不了的是小茹,说,你就不能少抽点吗?能饭吃?
我黑着脸说,他妈的,手气背,没劲,抽两口,提神。
林丽小嘴张开了,我受不了。
从我进来到现在,林丽的话不多,我们胡言乱语时,她更多的只是微笑。我看了她一眼,说,这有什么,打牌不抽烟那还算打牌吗?这光摸不抽是根本解决不了瘾的。
小子,什么光摸不抽,这里可是有小妹妹在,别说这些不雅言语。小李打了个西,说。
林丽的小脸顿时红了,我透过烟雾瞧着她,觉得她特有味,操,你想到哪去了,就你那龌龊的脑袋,整天像便衣一样,随时警戒着周围,一有风吹草动就暗喜终于有行动了,真不知道小茹怎么忍受得了呢,要我是小茹,早一脚把你给踢了。说完我就把目光转向小茹,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什么跟什么呀!关我什么事,你们不要扯到我身上来,坏东西。”
“哈,得,我们都是坏东西,你是好东西。”晕,我又摸到一张二万,没好气地说。
“碰!”小李再次发出噪音,“你别扯,谁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是什么德行呢。”
“我怎了。”
“切,装,你就装吧。咱们在学校那时候你是怎的,就不要我多说了吧。”
林丽瞧了我两眼,捂着嘴巴问小李:“你给说说,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我吞了一口烟,怪声怪气地说,老子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林丽看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说,那我就更想听听了。
我说,莫不成大姐对俺有性趣?
“去你的!”林丽从旁边伸过手来在我手背上捏了一下,这小妮子真是熟得够快,三言两语后就对我动手动脚了,就她那点劲,只能达到让我舒服一下而不会疼痛的地步。
小茹说,你别臭美了,以为自己是国宝。
“切,”我做了一个鄙视她的表情,“国宝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可是独一无二永远不会再有的品种,千万不要错过。”我说到后来已经是对着林丽,当然最后那句也是对她说的。
“少来,就你那德行,”小茹转过头对林丽说,“整一自恋狂在眼前。”
自恋狂没什么不好,没人恋就要自己恋,即使是有人恋也不如自己恋来得真实可靠。我承认我是个自恋狂,有什么关系?没关系!
小李也摸过一根烟,在小茹的责备目光下抽了一口,说,林丽你不知道,这家伙以前牛B得很。那次我们被辅导员训,只有他跟辅导员急,你知道他用什么来急吗?你一定猜不着,他妈的,我一直都服了他,他妈的他居然用大粪和性器官。
我说,那还不是小意思。我故作轻松,其实心里并不是这样,我只是掩饰着自己内心的烦躁,尤其是在林丽难以捉摸的眼光中,小李子,你别乱搞我的清白,小心我告你诽谤。靠,老子现在什么都没,只剩清白,再说小心我跟你急。其实小李说的没错,我也曾一度很欣赏自己,只是现在,我却莫名其妙的要跟过去划清界限。
“糊了!”小李嘴角挑着烟,两手各握一边把牌给开了,他娘的手气那么好,又自摸。自摸让他完全忽略了我把他称之为小李子。我摸摸裤兜,说,今儿手气背,改天再玩。
“哇,不是吧,刚上瘾你就不来了。”小茹的反应最大,跟一个正闭着眼睛呻吟的女人等待着对方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却晓得对方已经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能不大吗?
我笑了起来,说,这剩下的瘾你找小李帮忙你解决,相信他是乐意之至。今儿我是不玩了。边说边往外走,等哪天手气顺了,再战三百回合,小心你们的内裤都输给我。
“还早呢,不玩就坐会,再不在这里吃完晚饭再走。”
“谢了,甭操心,怎好意思打搅你们二人世界。”
不知是不是受到这话影响,一直沉默的林丽屁股在离开了椅子,说,我也回去了。
我们一前一后在小李两口子数着我的钞票时候出来了。我双手分别插在裤兜里,走起路来一摆一晃,一幅吊儿郎当样。林丽在后面叫住我说你上哪去?我回头说,我能上哪去,随便溜达。你呢?她说她也不知道上哪,又还不想回去。她的目光盯着鞋尖。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的是一双淡绿的高跟凉鞋,她完美干净白质的小脚把我给吸引住了。我有恋脚癖,尤其是对着女人的小脚特有感觉,那比艺术品还要艺术得很。有人说我变态,管他呢,在享受艺术品带给我舒适愉快的时候,我怎么有空去理会这些!
“要不咱们随便逛逛。”林丽察觉到了我的异态,用声音来“提醒”我。
“成,那咱们随便溜达溜达。”
就这样,我们一前一后相距三四米的距离就消失了。我在她的左边,她在我的右边。我们漫无目的地随着顺流逆流的人群。偶尔,我们的手臂会碰到一起,肌肤在摩擦。我发觉她似乎有点主动。这个发现让我心情愉快不少,怎么说可以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惹人烦的角色总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喜悦的分子在我们摩擦中诞生了,它从我们肌肤的毛孔中钻进来,在血液循环中一遍遍地带给我们一些微妙的体验。我们沉默着,似乎生怕一开口就会把这份微妙扼杀。没有人保证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成为真实,因此我们百般小心呵护着,一如照顾自家的孩子一般无微无至。呈现在我们前方的是不见底的路,我们的身影闪过一道道横向的岔口,向前走,至于哪里是停落点,我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后来,回想起与林丽的相遇,除了曾经相伴着走过一段路之外,其他的什么都不曾存在。对于她,留在我印象中的残影也就那么一点点。我只知道她叫林丽,其他的职业年龄喜好是否有男朋友有过几个男朋友老家在何处都有些什么人喜欢用哪个牌子的卫生棉是否对我产生爱意如此之类的都是一片空白。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她就象一颗在夜空中一擦而过的陨石,在我的摩擦中划下了一道美丽的亮光,成为我的流星。
我们在公园里完事之后,在我家的床上,她问我使用大粪和性器官来急的那码事。那些陈年往事,好象我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有一个屁眼,都从那里往外排泄,差别不同的是它的外形大小伸缩度和所排泄的物质形状质地稀稠浓度罢了,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同一码事。我那时候是想藉此来告诉那个辅导员,我们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大不了,不要在那里张牙舞爪。我大概地把这个告诉了林丽,至于性器官,我则没说,因为那时候她已经大笑着抓住了我的老二。林丽在床上跟平时简直是判若两人,她的目清眉秀青纯可人的外观彻底被抛弃。她热情似火,如喷发的火山,她的指甲掐进我的身体,她的小嘴唇像个饿坏的孩子无休止地咬着我,想完全地把我吞掉。
早上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事,是关于台风的。里面称今年迄今为止最好风级的台风将会在未来二十四小时在这座城市登陆。中午,老天果然拉下了脸,变得阴沉,风也刮起来了。我站在窗前,看着尘土甚嚣的天空,一起一落的是废纸残菜叶子,行人慌慌张张地闪过,向着各自的目的。整个原本有条有理的城市丢光了她的沉稳,慢慢混乱,然后空洞。一扇扇紧闭的窗户里,不知道是什么。
我妈给我挂了一电话,嘱咐我要小心台风。苍老的声音里是对我莫大的关切,在这混乱的慌张中,她的话就如一支镇定剂,让我糟糕的心情好起来。我先起了小D,想知道她怎样了,但终犹豫了。
像是印证这个时代科学的伟大与是实用性,台风如预报的那样准时降临鬼哭狼嚎的风夹带着豆子般大小的雨珠敲打在玻璃上,停电瞬间放眼之处皆是黑呼呼一片,恐惧划过我的心脏,我感到乏力,仿佛世界末日。
关于这篇文字,是时候告一段落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一些我们熟悉或陌生的事情,都有一个起因,经过,高潮和结局。生活就像一篇记叙文。在这里,我想必须得说说小D,我们也曾联系过,在分手已成事实,我们的联系不是留恋与否。而对于分手的缘由则归罪于我心目中没有一点她的位置。小D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淡若开水,像是述说一件完全与她无关的事情,她有资格这样,她就快结婚了,新郎哥比我帅比我有钱比我瘦比我性功能强比我更善于对付女人,至于是否比我还他妈的不要脸比我还不是个东西,那我就不清楚了。
“或许你的心中有我的存在,只是我感觉不到,你所处的方式是我所明白不了的。”
我想起那天她留给我的话。告别时候,我们互相衷心祝福对方。或许生活着,我们所留恋的只是自己,一如恋爱,爱的往往只是自己的感觉。至于林丽,虽然我不只于一次在小李那里出现,但却从不在见她,她已经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我们只是偶然的相逢在一起,各自谋取自己的需要,我跟她就如寒冬里两具冰冷的身躯,缠和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取暖。我明白这个时候,已经是换了一分工作。早在和小D争吵之前我就厌倦了那个工作,这份厌倦散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与那晚的那位美眉说起这些时间发生的这一切,我说我终于体会到了站在高峰处的感受。她说你一直都是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之中。她还说,我们生存在这座钢铁森林中,早就缺乏了先天,我们苟活着,半死不活的。她最后告诉我,生活就如一座密室,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惟有想方设法去钻个孔,从孔里获取生活的腐败营养,继续苟活下去。
是的,的确如此,也应当这般。台风肆虐后,城市角落里到处闪烁着清洁工忙碌的身影,一张张操着各种各样的脸谱重新活跃在城市的城墙上。很快,又将焕然一新。走在街上,我忽然想起成为我跟小D争吵的导火线“你到底救谁?我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往干净的道上吐了一口浓痰,他妈的,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