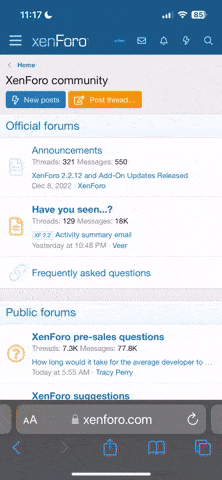母亲 你魂归何处
母亲,你感应到吗?我刚从寺庙烧香回来,缭绕的香烟徐徐升起,会融进你的灵魂吗?天堂的你能感受到儿子的哀思与低沉吗?
你永别的那天,我们把你在人间所使用过的衣物全部托付河水带走,你在天堂收到吗?夏天过后就是秋天了。我喜于秋亦怕于秋,我在秋天收获利润赏功庆酒时,没有你在场,我的心头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你在世时,每到中秋,我必回到你身边,自从你走后,中秋节我都没回过老家了。平日,当思潮翻滚难眠时,我会赶回老家,静立在你生前住过的房间发呆,那盏曾在风雨中摇晃着伴你挨家过户为我筹学费的煤油灯染尘变黄了,再没人动用过它了。生蛋的老母鸡随着你离去也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鸡窝空落着,再也不能吃到你亲自为我做的鸡蛋粥了。柴房还剩很多干柴,那是你生前气喘吁吁从山上背下的生柴,这些干柴足可解决数十天雨水造成的缺柴之苦。“有时记着无时日”,你这句朴实至真的话让我一生受用。沿着你曾走过的田埂,走近你生前弄过的菜园边,那菜园已杂草丛生,你走之后,青一色的菜园也荒凉了,影亦绝了。
虽然你一字不识,但你对何时适宜春耕冬种,何日是节假日、圩日都很明确;对“粒粒皆辛苦”理解、运用透彻得让我自愧不如,见着掉落在地上的饭粒,哪怕仅是几粒,你都会俯首拾起,并现身说法:“一粒米一滴汗,脚踩饭米,会盲眼的”,教育我们要懂得节约、珍惜生活。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是外乡人到我们山村开荒的高峰时期,有不少过客饥渴借饮,你常把留给我们不多的稀粥端出来,乐呵呵请他们吃。在“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年代,你如此大方,着实让我吃惊。在拌碗油粥都显得奢侈的年代,我好不容易从邻居处“弄”来一只鸡,正待宰解馋,你知实情之后,将它夺回送归主人,并赔礼道歉,我羞愧得来不及躲藏,自此时时记住要善身律己。
你把间或卖鸭毛、烂什所得的零星钱,还有年节亲戚给你的一点买糖钱,用碎布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将它们“冻结”在一只老式破旧木箱里,只有我们兄弟需交学费时,你才将它们“解冻”。当山村里的少男少女陆续外出打工之风刮起时,你不为之所动,顶住压力,背负债台,用瘦弱的身躯千方百计支撑着我们兄弟的学业,你面额上的条条皱纹换来了我们兄弟的张张奖状,我们先后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业。
你一生劳碌,以耕田为生,积劳成疾。直至我们兄弟参加工作后,苦苦相劝,你才将那一亩几分田转人代耕。在生活渐渐起色时,你却离开了我们!你走时极清醒,却没有半句遗言,只见眼角渗出几滴泪水。你已为我们付出全部,你那临终泪水该是句号;我们没有让你过上几年闲日子,你连最小的两个儿子结婚成家都没有看到就走了, 那泪水是许多未了却的纯朴心愿……
母亲,你在哪?我一直在跟踪,想起你魂归何处,我总是陷于迷茫状态。据说人走后魂归泰山,我于你走后的第二年直奔泰山,从山脚一直蹬至顶峰,我的腿居然没有明显酸软,没有累倒在半山腰,你是不是如生前一样在保护着我?泰山顶静秘幽森,分不清云、雾、群山。你的魂是否化作其中?偶尔钟声传来,想象着是你的回声,落暮时,从空中传来鸟啼声,是不是你从云端钻出来了?但瞬间又飞逝了……
尽孝当及时,莫待亲人魂归天堂空悲切。
母亲,你感应到吗?我刚从寺庙烧香回来,缭绕的香烟徐徐升起,会融进你的灵魂吗?天堂的你能感受到儿子的哀思与低沉吗?
你永别的那天,我们把你在人间所使用过的衣物全部托付河水带走,你在天堂收到吗?夏天过后就是秋天了。我喜于秋亦怕于秋,我在秋天收获利润赏功庆酒时,没有你在场,我的心头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你在世时,每到中秋,我必回到你身边,自从你走后,中秋节我都没回过老家了。平日,当思潮翻滚难眠时,我会赶回老家,静立在你生前住过的房间发呆,那盏曾在风雨中摇晃着伴你挨家过户为我筹学费的煤油灯染尘变黄了,再没人动用过它了。生蛋的老母鸡随着你离去也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鸡窝空落着,再也不能吃到你亲自为我做的鸡蛋粥了。柴房还剩很多干柴,那是你生前气喘吁吁从山上背下的生柴,这些干柴足可解决数十天雨水造成的缺柴之苦。“有时记着无时日”,你这句朴实至真的话让我一生受用。沿着你曾走过的田埂,走近你生前弄过的菜园边,那菜园已杂草丛生,你走之后,青一色的菜园也荒凉了,影亦绝了。
虽然你一字不识,但你对何时适宜春耕冬种,何日是节假日、圩日都很明确;对“粒粒皆辛苦”理解、运用透彻得让我自愧不如,见着掉落在地上的饭粒,哪怕仅是几粒,你都会俯首拾起,并现身说法:“一粒米一滴汗,脚踩饭米,会盲眼的”,教育我们要懂得节约、珍惜生活。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是外乡人到我们山村开荒的高峰时期,有不少过客饥渴借饮,你常把留给我们不多的稀粥端出来,乐呵呵请他们吃。在“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年代,你如此大方,着实让我吃惊。在拌碗油粥都显得奢侈的年代,我好不容易从邻居处“弄”来一只鸡,正待宰解馋,你知实情之后,将它夺回送归主人,并赔礼道歉,我羞愧得来不及躲藏,自此时时记住要善身律己。
你把间或卖鸭毛、烂什所得的零星钱,还有年节亲戚给你的一点买糖钱,用碎布将它们层层包裹起来,将它们“冻结”在一只老式破旧木箱里,只有我们兄弟需交学费时,你才将它们“解冻”。当山村里的少男少女陆续外出打工之风刮起时,你不为之所动,顶住压力,背负债台,用瘦弱的身躯千方百计支撑着我们兄弟的学业,你面额上的条条皱纹换来了我们兄弟的张张奖状,我们先后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业。
你一生劳碌,以耕田为生,积劳成疾。直至我们兄弟参加工作后,苦苦相劝,你才将那一亩几分田转人代耕。在生活渐渐起色时,你却离开了我们!你走时极清醒,却没有半句遗言,只见眼角渗出几滴泪水。你已为我们付出全部,你那临终泪水该是句号;我们没有让你过上几年闲日子,你连最小的两个儿子结婚成家都没有看到就走了, 那泪水是许多未了却的纯朴心愿……
母亲,你在哪?我一直在跟踪,想起你魂归何处,我总是陷于迷茫状态。据说人走后魂归泰山,我于你走后的第二年直奔泰山,从山脚一直蹬至顶峰,我的腿居然没有明显酸软,没有累倒在半山腰,你是不是如生前一样在保护着我?泰山顶静秘幽森,分不清云、雾、群山。你的魂是否化作其中?偶尔钟声传来,想象着是你的回声,落暮时,从空中传来鸟啼声,是不是你从云端钻出来了?但瞬间又飞逝了……
尽孝当及时,莫待亲人魂归天堂空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