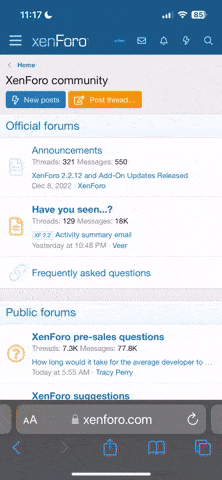azhong339
初中三年级
- 注册
- 2006-05-14
- 帖子
- 526
- 反馈评分
- 0
- 点数
- 0
- 年龄
- 63
日记 2005年9月11日晚
近日,多次想在晚上8、9点钟左右给父母亲打电话,但不知为何都是在近晚10点以后才想起来,这个时候父母亲肯定是睡觉了。
我父母亲睡觉都很早,特别是我母亲,住在农村小镇,晚上没有什么娱乐,劳累一天,吃过晚饭就冲凉,也就早早地上床做梦。
家乡虽说靠近海边,但地处广东西南山区,社会文化经济落后。改革开放20多年,家乡经济水平相对广东省的整体发展来说相差很大。平日里大多是老人孩子在家,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做生意。有很多人家在外面赚了钱,就回家乡建房。所以不论是镇里还是在村里,建的住宅小楼不少,同时道路交通也比以前顺畅了许多。
父亲刚转业回家那会儿,先是住在公社院里的房子,1992年才在镇子里建房,位于镇北,依山坡而建,门前有一条高州至广州的省级公路经过。建的是两层楼房,中间有个天井,一层有厅、厨房及杂物间等,二层住人,屋顶有水箱和鸽棚。门口种有三棵龙眼树,每年结二、三百斤龙眼,很好吃。前院不大,搭个棚子,供人乘凉,亲戚朋友常来访,在棚下喝茶、打牌。后院是个陡山坡,时常有蛇等小野生动物出没,养有鸡鸭,植有20多棵果树,有10多种南方水果及瓜菜,随时都有水果吃,吃不了的每年还能卖些钱。家里养有狗和猫,狗看家护院,猫经常在后院抓只老鼠、蛇、鸟或什么虫子在家里玩,不吃,玩死了就放在墙角不管了……
我结婚那年,带着北京媳妇探家。记得刚到家,父亲给煮粥喝,见吃的咸菜很特别,问我是何物做的,我说是芒果,她很惊讶(那时北京很少卖,十几元一斤)。看到家乡山清水秀高兴;见到粗大的石竹高兴;看到橡胶林高兴,照相,假模假样的当回橡胶女,乐不思返。
女儿尧尧两岁时第一次回老家,从北京到广州好好的,从广州到老家一上火车大哭不停,谁劝也不行,快到那霍站时哭泣得更大。到站下车,我母亲抢过尧尧就抱着,尧尧立即不哭了,我母亲抱着尧尧,不停地亲着尧尧,尧尧双手搂着她阿婆脖子不放,从车站到家不放手,其他人谁抱都不行,搂着阿婆紧紧地,小脸亲着阿婆的老脸,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和不解,这可是祖孙二人第一次见面!
尧尧第一次见到遍野的含羞草好奇,第一次回到老家见什么都高兴,饿了就到后院,上树摘水果,吃个够。
尧尧的舅舅也跟随回了老家一趟,玩了5天,吃了5天家乡饭,明白了什么是正宗的广东岭南客家菜,长了5斤肉,赶紧先返京了。
我探家次数不多,但每回去一次,感受都不同,心情都很复杂。一是见70多岁的父母亲老了许多,作为儿子,又不能尽赡养义务,心里内疚。二是看着自己的家还是那样变化不大,自己无为,心里歉疚。
父亲在家乡解放后不久就参军去了,听母亲说是结婚以后参的军,走后好几年才回家一次,父亲30多岁才生的我,是母亲在家乡将我带大的,那时候家里生活很苦。在我4岁之前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概念。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到“北方”探亲,记忆中的第一次和母亲到部队探亲好像是到武汉,后来得知是住在武汉钢铁厂附属医院。当时正是**期间,父亲是驻厂军代表。当年,父亲所在部队是武汉军区空军第十五军空降部队。
我实在是记不清几岁到的武汉,只记得常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的砂堆上玩。住的是楼房,而且有电梯。有次与一名小朋友开电梯玩,不知按错了哪个键,电梯卡在楼层之间不动了,两人在电梯间里大哭,急得母亲楼上楼下的乱叫,从白天到天黑,大人们忙碌了大半天才从电梯箱里将我们拉上来。过去快40年了,母亲提起此事还后怕,见到电梯就两腿哆嗦,一再提醒我今后买房,千万不要有电梯的。
那时候,常有高音喇叭的汽车在大街上来回跑。隔几天就有军车押着要枪毙的死犯经对医院门口的大街,犯人被绑在卡车前帮上,后脖颈插着牌,胸前还挂着牌,写着什么罪,名字上面画个大红叉,死犯个个看上去面目可憎,给我印象最可怕的是一些从口中吐出舌头的犯人了,身后左右各有一名拿枪的军人押着,车上还站着两排拿枪的军人,表情严肃。车子慢慢地开着,在车队的前面有一辆广播车,不停地说某某犯了什么罪,判处死刑……。街道两旁围观的人很多,只是静静的看着,车队过去了,人们也散去了,街道又恢复了原来的喧闹。
有时大人们也带我上街,看到飘在空中的气球好生奇怪――为什么我吹的气球就飘不起来呢?
父母带我参观过一个教育展,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印象很深,后来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中有这篇课文。
还记得有几桩淘气的小糗事:因好奇将一支不出水的圆珠笔芯油墨吸进肚子里,恶心了好几天;上厕所不小心将一支叔叔送的新钢笔掉进了茅坑,伤心了好几天;有一次在院内砂堆玩耍,正玩到兴头上,附近锅炉房的开水锅炉突然爆炸了,吓了好几天;还有一次母亲让我热牛奶,由于贪玩忘了牛奶烧干了,把锅也烧毁了,母亲骂了我好几天……
也有高兴的事儿,每天都能吃饱饭,不用饿着;吃了些我从没吃过的水果;还有牛奶、点心等。第一次进大城市,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到高楼,第一次住进楼房,并乘过电梯,还有很多的第一次……如:第一次知道电灯,一拉绳子就亮;知道什么是水龙头,只要一拧开关就出水。当时想:这若是能安在老家的房子里多好啊!
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是母亲带我去北方探望父亲。那时我还很小,实在不懂事,在火车上我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大声叫喊着要吃鸡腿,吵闹了不知多长时间才得到。现在,每当母亲提起此事,老泪在眼睛里打转,可想当时这事对母亲来说是很棘手、很为难的。长大了,懂点事了,心里想起,总感觉对不起母亲,现在我一看见鸡腿就犯怵。
记不清随母亲有多少次到部队探亲。有时有父亲陪着,一次,父亲带着我们在中途下了火车,就住在铁路旁的平房里。晚上,火车轰鸣声、气笛声,阵阵入耳,难以入睡。天未亮大人把我叫醒,草草地吃了早点,就摸黑上了火车。
后来长大了点才知道那是广西玉林火车站,住在王叔叔家。王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记得我家搬在湖北云梦隔卜武空1114盐厂时,王叔叔多次来探望,并且带来很多糖果,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就是他给我的(那巧克力的香甜口味实在是印象太深了)。有一年我探家,王叔叔还来看我,他已退休了,老了很多,但还是显得很亲切,他说还是住在玉林火车站,我总想有一天要去探望他老人家。
还记得一次父亲送我们返回家乡途中,火车在一个小车站停下,父亲下车给我们买水果,结果火车停的时间短,父亲没上车,火车就开走了,急得我大哭,母亲更是急,与列车长联系,在下一站就下了车等着父亲。后来父亲是延着铁路走来的。我们在车站的安排下坐了一列路过的货车,在尾部小车箱里坐到终点站。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父亲下车的车站是河唇站,父亲见车站有荔枝卖就下车去买,结果误了时间。
当年,由于交通不便,每次探亲路线图是这样的:从石牌垌走到黄岭,坐汽车到水东,在水东大伯家住几天,再坐汽车到湛江,然后再坐火车到父亲服役部队所在地附近的火车站,坐汽车到驻地。返回家大多是坐火车到湛江或茂名站后坐长途车到水东,在大伯家住几天后再坐车回黄岭,从黄岭走回石牌垌。这对母亲来说,一个南方没有文化而且方言不通(我是讲涯话佬)的农村妇女带着孩子到北方探亲是很辛苦的,何况母亲患有严重的晕车症。
我的母亲晕车很严重,有时像要虚脱的样子。我也晕车,一坐车就难受。我的女儿尧尧也晕车,有一次坐飞机,脸煞白,胃里的胆汁都吐出来了,这也许是遗传。
我小时与母亲在老家生活,期间有几次到父亲部队探亲,长到7、8岁才正式离开家乡,随军到湖北省应山县广水公社,在部队驻地那儿一个小山村的小学上学。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搬到湖北省云梦县隔卜公社,住武汉空军1114盐厂,在隔卜公社上学,至1979年高中毕业,年底参军到北京。1982年初利用在外学习放寒假期间探家,回老家过的春节,这是我离开家乡12年后的第一次探家,时年20岁。记得那次探家,没让家人接站,凭着儿时的记忆,准确“摸”回老家,着实让父母及亲友惊喜,少小离家,回来已是个壮小伙子,家人当然高兴,此后每年都要探次家。结婚后因为各种原因,探家就少了,这是我心中一个理不清的结。
离开家乡时虽说还小,但家乡给我儿时留下很多美好记忆,这记忆是永恒的,这记忆是深刻的,这记忆难以忘怀,这感情难以表达。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电白县黄岭公社水西大队石牌垌生产队――这是当年的称呼,现在全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黄岭镇水西管区石牌垌村。
我出生在贫农家庭,长在农村。虽说父亲是军人,但父亲远离家乡在外地服役,家里的事关照不上。所以,我基本上是母亲带大的。
母亲说我是很有福的孩子,吃母乳到一岁大,小时候白白胖胖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母亲的话是可信的,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付出最多,对自己孩子都是赞美的,认为自己孩子是最好的。何况当年父亲不在身边,只有母亲带我,当年生活很苦,把我带大不容易。所以,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
我的父辈排行是这样的:我父亲老大,两个姑妈在中间,幺叔最小。我不知母亲有多少兄弟姐妹,每次探家我都犯晕。后来看家谱,因只记男不记女,很多亲戚无从核实,这就不说了。
我阿婆瘦高个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头,头顶掉光了头发,边上的头发稀薄没几根,并时常头痛,头皮是花的,有疤痕。听大人们讲,阿婆年轻时,有一次在地主的地里干活,因故被打,一锒头打在脑门,差点死了,从此头就这样了,没法治。我长大点,记得父亲多次找医生看,没治好。
年幼时,母亲背着我下地干活;年少时,母亲出工,阿婆就带我。阿婆没有留下张照片,30多年了,她的模样已淡去。她带我到8岁;也带过我大弟汉平,那时汉平还小,想必没什么印象;没带过小弟爱民,他就不知道阿婆什么样了。
阿婆好像是在我10岁左右去世的,当时我家在湖北省应山县广水公社很远的一个山坡军营里,当年父亲是武空15军应山飞机场地勤汽车连指导员。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阿婆死了,母亲眼泪出来了,我听了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父亲一人探家料理后事,记得那是5、6月的季节,父亲从老家回来时带了很多家乡的水果。
我没见过爷爷,母亲说她嫁到这儿就没见到,说明爷爷死的早,父亲从没给我讲过爷爷的事。听大人们讲,我爷爷是个有点文化的人,当过私塾先生,所以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小时不懂事,因为好奇,又没什么好玩的,就偷偷地拆毁过很多爷爷遗留下的书,那些书都是线装的,很精致。我后来探家时总想找这些书,没了,一代穷书生,其后人没几个读书像样儿的,可叹!
我幺叔是我最亲近的人,在我年幼时,幺叔很疼爱我,时常护着我,时常带我玩耍。如做风筝、捕青蛙、采野果,背我过看病……,我父亲不在家,他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是顶梁柱,是我靠山和依托。
幺叔生有三男二女,我在家乡时,已有大堂妹和两个堂弟,后来两人是我到“北方”后出生的,就不熟了。我第一次探家时,大堂妹已出嫁到邻村的一户人家,其丈夫当过兵很能干,一家生活水平在当地还算可以,建了楼房。最近几次探家,只见二堂弟在家守着老宅种地,老实本份。幺叔和另外两个堂弟在阳江市以养鱼为生。
姑妈家住高州县龙潭公社,我有一表姐三表弟,其中一个表弟阿狗仔是个残疾儿,与汉平同岁。当年姑妈很疼爱我,母亲常带我去探亲,因为路走熟了,有时我自己一个人就去了。有一次,傍晚我一人走到姑妈家,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吓得我直哆嗦,但还是因为饥饿战胜了恐惧。为了一碗饭,把家人都吓坏了。现在姑妈家搬到高州市,在市里建有六层小楼,一家生活都很不错。
我外公瘦小个子,精神很好,主要特点是他有几根眉毛特别长,人称长寿眉。人总是乐呵呵地,爱说爱笑,人很勤快,能干。对我很好,小时母亲常带我去外公家探亲,外公家做的饼很好吃,外公家座落在罗坑公社的一个小山村,要走很长的路,趟几条小河,翻过几座小山丘,路过好几个村庄。村庄坐落在一个山丘上,外公家门前有一口井、一片小竹林、一个不大的水塘。幺舅带我和表弟、表妹们到附近的山野玩耍,记得村边有一很大很长的引水渠,我们在那儿抓过鱼虾。
听母亲说,外公结过两次婚,母亲是长女,亲外婆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是跟着后外婆长大的……。关于她儿时在娘家的事,零零星星的,她说的不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她对外公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好。我母亲是敢说敢干敢恨敢爱的人,内心有什么事都表现出来。但作为女儿,对其父亲还是很孝敬的。
外公身体很健康,我探家时,他80多岁了有时能走很长的山路到我家来。外公是2003年去世的,享年??多岁,去世时亲戚告诉我父亲,我父亲不信,下葬后的次日才知道是“真”死了,一个人才跑到坟头跪下大哭,成了大家的笑柄。这说明外公生前一直是很健康的,去世前后没有给家人带来麻烦。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城里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阿姨。到村里来教大人识字,并教大人唱歌。那时,母亲常抱着我去上课,这个阿姨在我印象中长得是最漂亮了,与这里的村姑反差很大,白净透红的皮肤、粗长黑亮的辫子,大大的眼睛,漂亮的衣服,高贵的气质,和蔼的神态,我从没见过,说话很好听,和广播电台一样的声音,宏亮并且听起来甜甜的。她走到哪儿,总有一大群小孩子(也有我)跟在她后面,村民总是围着她说些家长哩短……她总是笑着,不知为什么她总是有那么多的高兴事儿。她是哪儿人?从哪儿来?无亲无故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至今也不知,也没问过。
这个阿姨与我母亲同姓周,日子长了与我母亲成了好姐妹,她时常给我些吃的。后来她走了,到黄岭公社饭店工作。走后,母亲常念到她,有时带我去过探望她,在我印象中,只知道周阿姨那儿有饭吃,所以,我有时饿极了就自个一人走10多公里山路到黄岭找周阿姨,住上几天,吃饱喝足了才回家,搞得家人很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左右,周阿姨离开了黄岭,不知道又到哪儿去了,再也没见面,我时常想念她。
所以我参军后的第一次探家,一回到家乡即刻到处打听周阿姨的下落。自从周阿姨离开了黄岭,大人之间就没再联系过,好几天才得知她在茂名石油公司工作,我即刻去探望她。她与十几年前比,变化很大,老了许多,发福了许多,差点认不出来。没变的是她还是那样美丽,依然显得气质高贵,并增添了几份慈祥。
第一次见面,周阿姨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实在是感动(女孩很漂亮,是羊角公社人,与她见过一次面通过几封信后再没来往)。
我家乡位于广东省西南山区,靠海,北回归线以南,受亚热带海洋气候影响,四季不分明,而分旱季雨季。在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雷电轰鸣,常有台风经过,暴雨成灾。旱季雨水不多,但河溪水流不断,一年总是绿油油的。家乡是丘陵地带,红土地,山不高,水不深。家乡离大海约有40多公里的山路,村离县城水东镇有90多公里。我的家宅位于村东南隅,土砖墙,青瓦房,是典型的广东岭南农舍,正房中间为厅,侧房住人,两侧厢房设有橱房、杂物间、耕牛棚、或放些农具、农物、柴草等,中间有个大天井,正门朝东,门前有一猪棚,一水塘,一条小溪,小溪里有小鱼虾,并时常也有毒蛇出没。村子里有很多的果树,龙眼、荔枝、波萝密等南方水果。村和村之间很近,人多地少。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种两季水稻,因雨水多,田里小鱼虾也多,青蛙也多,成天叫个不停,时常夜里幺叔带我去田里抓青蛙。离村不远有一条河,因我村在河西岸,所以村所在的地方叫水西,归黄岭公社。河对面叫水石,属于那霍公社。大人们常在河里抓鱼,小孩子常在河里游泳或在河滩放牛、玩耍。
村口与河之间有条小路相通,路边竖有一石头,像块石牌,孤伶伶插在土里,露出地面一人多高,所以我村名叫石牌垌。
相传,这石牌是我村的象征,是福祉,是命根,有很多动人的古老传说。此石牌有仙气,常被他人偷盗。相传很久以前,一次石牌被妖魔偷走,全村老少奋力相争,夺回石牌,再次立于村口,村民日月守护着,至今依然屹立在哪儿巍然不动,守望村民的出行,保佑村民的平安。在我儿时,这石牌边有村口通往河边的小路,我走亲访友,后来上学都路过,有时在石牌边玩耍,在儿时的心目中,这石牌是神圣的,同时又显得非常神秘。也许我那时还小,大人们没有给我讲过这石牌的来历,这石牌是什么?为什么会孤伶伶地立在那里?
以前村民出行有三条比较宽点的泥土路,一条到黄岭,一条延着河边到高洲的龙潭(一段泥土路、一段柏油路即广州至高州省级公路,也可到那霍),一条就是走石牌边的小路过河到那霍,(另有很多已记不清的山间“小路”,我到龙潭姑妈家走的就是这种小路)。现在人们外出走路的不多了,经济发展各种车辆的使用,村民就很少再走石牌这条路了,石牌周围变成了农田,所以这条路也就没了。现在的村民要到河边很不方便,只能走弯曲的田埂。
村前的河,大人说以前常犯水患,约在我5、6岁那年,政府出资,动员沿岸百姓清理河道、加固堤坝、疏通河水。那时青壮年劳力都参与到了这劳动大军中,只见河的两岸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幺叔也给我做了个小扁担和一对小箩筐,带我到工地,从河中挑卵石到堤坝上。天天都去,我也争工分。那时干活很苦,不是暴晒就是雨淋,工地上没遮没挡,在工地也有少年参加,然而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也就我一个。那时我小,挑担子晃晃悠悠,为此闹出不少笑话。从那时起也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出工了,成了个小社员,挣工分。后来上小学,课余没事也常下地干活或帮家里做些家务。
已过去30多年了,长辈们见到我就常提起当年此事,而母亲在一旁总是伤心的样子,眼里含着泪,有时冲着人们大声嚷几句,然后独自一旁沉默不语。
一次探家,与母亲一起路过这条河,她停下来站在堤坝上,拉着我的手,看着流淌的河水,老泪也流到了她老脸上,说着一些过去伤心的话,母亲好像对我一辈子都很愧疚,好像让我受了不少苦。这就是我的母亲,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当年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丈夫不在家,过日子是很难的,她所受的苦能对谁说?谁能知道?谁能分担?
我每次探家,一是必看石牌,二是必看这条河。这条河给了我童年快乐,也给了我童年许多磨难。河水始终都是清澈见底,鱼虾在河床下的鹅卵石间漫游,翠绿的河滩如同铺了一层草甸,河边有不停转动的水车,时常见人赶着一群鸭、鹅从河面经过,儿时常与小伙伴在这条河一起放牛、玩耍、游泳、抓鱼虾,渡过每一个快乐时光;而这条河也让我流过汗水,让我母亲铭刻着苦的记忆。这条河现状与儿时大不一样了,现在除了河水还是哪样清澈外,鱼虾已不多了,也很少见村童在河里戏耍,以前得趟着过河,现在河上架了一座简易木桥,桥头有收费的,半天见不到要过河的行人。
小时候常跟着母亲走亲戚,大多要过村前的河,过河后还要走好长的路,有的还要翻山越岭。记得深刻的山路是到铁打水姑妈家。铁打水座落在一高山的山坳里,山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清澈的溪水潺潺不断,飞禽走兽,花草鱼虫,山珍野果,山水如画,一派热带雨林景象,如同人间仙境。村子不大,与其它村子相隔很远。儿时姑妈家那儿养有梅花鹿,野猪常到村边骚扰。表哥常在村后的沼泽地里插些树桩子,没几日就长出很多的木耳,做菜很好吃。当年,这儿对我没什么好的印象,因为要走一整天的山路,从一大早出门,下午才到,累!特别是到了晚上,感觉是阴森森的非常可怕,但是,我每次去那儿都能吃上很多的山珍、野果、蜂蜜什么的,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条路线是这样的:出家门、过河、过水石、过那霍、再过条河、穿过几个小山村,路上有一小水库,漫长而又弯弯的山路。我小时候没敢独自一个人走这条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村民进出不便,路人很少,至今也没能通车。
儿时,母亲说要走亲戚,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不让背,自个走得欢实着呢。
那时,只要大人带我走过一次的路,都能记得,只要目的地有好吃的,就记得更清楚。为了吃的,一人走到黄岭找周阿姨,吃饱后再住上几天才独自回家。一人走到龙潭姑妈家,玩几天,玩够了才回家,哪怕是走夜路。这样的事不止几次,那时候母亲白天出工了,家里没得吃的,肚子饿,有时告诉阿婆一声就走了。我知道哪条路好走,哪条路目的地有什么吃的,只要有好吃的,哪儿我都敢去,无需跟大人走。
我年幼时,晚上母亲有时对我说很多话,有很多我听不懂,但很愿意听母亲讲故事。讲的都是些鬼神,一是水鬼,二是山鬼,都是吃人的鬼,讲得很多,讲得很经典,我还记得一些,其内容从古至今没有书记载,在我上中学时曾经整理过,后来因多次搬家等原因,书稿早已不见。
母亲说我是从河边的草地上拣回来的,我信了,后来有了弟弟,才知道母亲说的不对。
母亲说她年轻时在砖厂干过,在水泥厂干过,后来嫁到这里,当妇女队长。母亲很勤快,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在我记忆中,母亲好像没觉得累的时候,母亲心地善良,性格泼辣耿直,敢说敢干。
幼儿时,我常在家里的土地面上爬滚玩耍,沾得满身鸡屎狗屎,我头上、屁股、身子、腿脚上长了很多的脓泡,苍蝇在脓泡疤口上爬来爬去,赶都赶不走,现在全身还留着很多这些疤痕,这是我1、2岁时给我留下仅有的记忆。大人说:我幼儿时鼻涕流到下巴,也不擤,这事常成为大人的笑话。
4岁大时,走到一个粪池边时,不小心掉到粪池里,呛了不少粪汤,好久大人才发现,大人们是怎样把我拉上来记不得了。醒来时只知我爬在地上一口倒扣着的大铁锅上面吐粪汤,幺叔看我清醒过来了就抱回家。家人给我冲洗了好久,我不停地哭,阿婆不停地骂着母亲,母亲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给我洗身子,让我喝了好几大碗药汤,上吐下泻了好久。第二天阿婆见家里实在没什么吃的,就让堂妹陪着我,拿个大竹筒,在附近村子里挨家挨户讨些米回来,煮稀粥吃了好几天。这就是我要饭的经历,终身难忘。
最让母亲伤心的,而是在我5岁左右大时得了一场大病。后来听母亲说,我当时发高烧42度有好几天昏迷不醒,母亲到处请大夫,都没法治,有人劝我母亲放弃。深夜病情加重时,母亲一人摸黑背着我到水石看医生,那医生给我打了针,灌了药,很久不见效,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没救了,准备后事吧。母亲急了,说无论如何也要治好孩子病。母亲要了些药,深夜又背着我往回赶。水石与我村有十多里路程,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水流很急。但母亲还是以最快速度赶回家(这条路我走过,白天走都很难,深夜里一个女人背着个5岁大的病孩走这路不可想象),回到家叫醒幺叔,让幺叔背着我到黄岭公社医院,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我记得,当我醒来时第一句话是:阿妈,我要吃酱油泡饭。对我来说,这是最好吃的了,虽说味道与我平时吃的有所不同,可能是因生病,舌头味觉并没有感到有多香。病好后,幺叔就背着我回家了。到家时,放我下地,看到幺叔后背湿透了,不像是汗,一闻才知是我尿的尿。
那时,我已很久没让大人背我了,因为我自认为也是大人,之前我背过堂妹、堂弟。这次让幺叔背了,还在他后背尿尿,感到脸红。这场大病差点要了我的命,不是母亲的坚持,也许我就没了。幺叔一家也为此着急,让我一生感激不尽……
从那以后,除了胃有点毛病,并时常脑子有点犯晕,其它的我没再生过大病。
我父与幺叔虽说分了家,但两家还是住在祖父留下的屋子里,阿婆也和我们一起住,实际上还是一个家。后来我家随军后,屋宅由幺叔住了,幺叔赡养阿婆,并送终。我家在当地还是比较不错的人家,每隔一段日子,父亲总能寄回些钱和粮票、布票什么的,但每次到北方探亲这么来回一趟,几年的积蓄“都交给了铁道部”(母亲语)。在当年,村民生活都很苦,收割粮食后交公粮,生产队留下的就不多了,年底分红,每户分不到多少粮食,折算下来工分也就几分钱一天。
正因为当年家乡生活太苦,交通闭塞,人多地少,物资匮乏,村民终日为衣饱所愁。所以很多村民在外谋生能在外安家定居的,不愿再回家乡。我家随军在湖北定居后,父母就不愿让我再回去,也不愿提家乡的事,除了因阿婆去世,父亲独自回去料理后事外,全家十多年没探过家,至到1979年大栽军,父亲转业不得以才回家乡,但还是不让我跟回去,让我参军远离家乡。
听母亲说,在我还没出生前的那几年,没吃的,树皮都吃光了,那个村都要饿死不少人。后来政策有所变化,日子才有点好转,至少逢年过节偶尔还能吃上一两顿饭。当时虽说每户人家有几分自由地,种点菜、养些鸡鸭猪什么的,但还是很苦,煮的粥都能数得清米粒,大多是番薯就咸菜,时常为一日柴米油盐发愁。
有两三次晚上,随幺婶一起上山偷过柴(那时的山、田都属于生产队的)。晚上在山里走好远,黑灯瞎火的,割几镰刀就赶紧帮,挑起担子就往山下跑。那时没鞋子穿,光着脚,回到家时,脚掌扎了好几个洞,痛也不敢叫,实在受不了,再说这人群中,就我一个小孩子,母亲也反对我去,两三次后再也不去。然而,生产队分的那点柴,绝对不够烧的,无奈,只好白天到田埂、沟壑旁割些草回来当柴用。
我是6岁上的学。学校是什么样子就不说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的小学校比我们学校好多了,那儿毕竟还有桌凳,我们连桌凳都没有,下雨时屋里比屋外下得还欢。
在家乡上学的记忆不多,只记得一年级第一堂课,老师就教我们写5个字“毛主席万岁”,歪歪扭扭地,放学跑回家拿给母亲看,会写字了,高兴,后来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的小学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几次到“北方”探亲,随军后在当地农村学校上学,由于方言差别太大,老师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老师和同学都听不懂并取笑我。一、二年级就没怎么正经上,不得不复读二年级。实际上,我在小学没学到什么。特别是语文课,可以说就没学,一上语文课就头痛,见拼音就晕,所以我至今还是吐字不清,发音不准,在正规场所发言就脸红、流汗、哆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毛病有所好转。但写个文字材料总是语句不通,错字连篇,表达能力差,这辈子不会有进步了。
我的爷爷是个书生,父亲上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母亲从没上过学,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的就认得银纸(方言:即现金钞票)上的数字了。在我很小时候,周阿姨来到我村,教大人识字唱歌,母亲很积极,每堂课都去,但除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的也没学到什么。
……
儿时的记忆还有许多快乐事。
最高兴的莫过于过年了,有新衣、有好吃、有炮放、有戏看、走亲戚、与小伙伴玩游戏……。人们于节前就准备着直到元宵节,都在忙碌着快乐着。过年时每家每户都早早地备着鸡鸭鱼肉,放在祠堂祖先牌位前,全家人在祭台上点蜡烛、燃香、鞠躬,祭祀祖先,然后许个愿,亲人相互说些祝福的话。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长辈给晚辈发红包,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或放炮竹,或说旧年中的家长里短、展望新年前景,或玩牌游戏,其乐融融,守夜等待着新一年的到来,寄望着新年带来好运。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早早地起床,打开家门,放鞭炮,邻里乡亲互祝新年。过年时家家都做“鸭麻圆”吃(即汤元,无馅、用老母鸭顿汤煮,特香,是典型的岭南客家风味),并做些饼以备走亲访友时相互赠送。连续十来天都是走亲访友或亲戚来探,好不热闹。有时有舞狮队来门前表演,锣鼓喧天,这时,家主人拿一红包悬挂在高高的屋檐下,顿时只见瑞狮高昂着头,舞动着身躯,慢慢地靠近红包,用嘴衔着红包取下来,向主人示谢意,对瑞狮的表演,围观的人们报以掌声,红包中的钱不在多少(有时红包里放的是饼什么的),大家都是图个乐。
说起热闹事,印象深的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村里的人家娶媳妇,那气氛就像是全村的喜事一样,小孩子们都跑去看新娘,抢喜糖,好不热闹。
另一个是鱼塘起鱼,当年鱼塘都是生产队的,打起的鱼家家都有份。大人们头几天就准备了,当天只见男人在水塘里下网打鱼,鱼在塘里跳跃,岸上的人们笑逐颜开,女人拿来盛鱼的家什,小孩子在水塘岸边帮着大人抓鱼,人们欢叫着,开始称鱼分鱼,末了每家都拿着分到的鱼回家,晚上,全村弥漫着家家户户做的鱼香味,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有好吃的就高兴。
清明节,大人带着小孩子扫墓祭祖,是必做的,接着就是一年农忙正式开始了。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做很多的粽子,四棱的、长条的,形状各异;大多是肉馅的,味道各异,很好吃。走亲访友时相互尊送,能吃很长时间。
还有一个重要节日是中秋节,月饼是最好吃的,农家自己做,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五花八门,各家品味各不相同,既好吃又好看,口感香甜。现在再好再贵的月饼也不如那时的好吃,遗憾的是再也吃不上了。
再有就是与小伙伴到水田、溪河、水塘里抓鱼虾,捕青蛙,还经常到河里游泳,到已收割田里拣稻穗,进山里采野果……。
每年春夏季有很多水果吃:龙眼、荔枝、波箩、芒果、香蕉……品种很多,虽不是随便就能吃得上,但总能吃个够。
晚稻收割后,开阔的田野就是我们孩子放风筝的天地,风筝都是自己做的,造型简单,图案素雅,用竹条做龙骨,糊上纸,后背再绑上个竹片弓,风一吹就响。人们比着谁的风筝大,比谁的风筝好看,比谁的风筝声音响亮好听,比谁放飞的高、飞的远,比着放飞心情、放飞快乐。有时天上风筝发出的声音很响亮,传得很远,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北方人不会做,我在北方30多年从未见到。
……
以上是我儿时在家乡的部分记忆,随着时光的流失,很多记忆已逐渐淡去。
现在的家乡变化很大,虽然与广东其他地区比有些差距,但与过去比还是有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了,楼房多了,果园多了,路好走了,汽车多了。我离开家乡在外谋生,很惭愧不能为家乡建设做点什么。
石牌垌变了,但很多老人没了,儿时的小伙伴变成中年人了,不认识村里的青少年了。山上的橡胶林少了,深山里的大树没了,河鱼没以前多了,田里的青蛙很少见了,以前哪不分男女的路边厕所没了,村民见什么吃什么的习惯也改了,小学校园也变了……。不变的有我儿时说的家乡方言土语(涯话),不管何时何地,家乡话总是那么亲切,永生难忘!不变的还有记忆中的老宅、老井、水塘、小溪、河水;还有那永远不变的碧水蓝天以及永远淳朴的民风……特别是村口那座石牌,她还是哪样静静地孤伶伶地立在哪儿。像是站在村口守望游子归来的老人,任凭风吹雨淋日晒,日日夜夜总是巍然屹立在那儿,告诉外出谋生闯荡的村民:有亲人在惦记,有神灵在保佑;使游子不会孤独,不会迷失。我是她的游子,自幼随父母远离家乡在外谋生,成年后又独自在京城做事,生活习惯已改变,儿时记忆已淡去,但石牌依然在我心中,永远还是那样既神秘又神圣。
我每当怀念家乡时,就想起这石牌和村前的河,童年记忆总是显得很美好并充满着梦想,同时也因为我出生在这如此美丽的家乡而感到自豪。这就是我的家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走到哪儿我总是怀念她、赞美她。她在我心中总是哪样伟大、慈祥。我的祖祖辈辈在这儿生生不息,感激她养育过我,儿时的记忆在我心中永恒。我衷心地祝愿她越变越美丽、越变越富饶!我永远地祝福她!
近日,多次想在晚上8、9点钟左右给父母亲打电话,但不知为何都是在近晚10点以后才想起来,这个时候父母亲肯定是睡觉了。
我父母亲睡觉都很早,特别是我母亲,住在农村小镇,晚上没有什么娱乐,劳累一天,吃过晚饭就冲凉,也就早早地上床做梦。
家乡虽说靠近海边,但地处广东西南山区,社会文化经济落后。改革开放20多年,家乡经济水平相对广东省的整体发展来说相差很大。平日里大多是老人孩子在家,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做生意。有很多人家在外面赚了钱,就回家乡建房。所以不论是镇里还是在村里,建的住宅小楼不少,同时道路交通也比以前顺畅了许多。
父亲刚转业回家那会儿,先是住在公社院里的房子,1992年才在镇子里建房,位于镇北,依山坡而建,门前有一条高州至广州的省级公路经过。建的是两层楼房,中间有个天井,一层有厅、厨房及杂物间等,二层住人,屋顶有水箱和鸽棚。门口种有三棵龙眼树,每年结二、三百斤龙眼,很好吃。前院不大,搭个棚子,供人乘凉,亲戚朋友常来访,在棚下喝茶、打牌。后院是个陡山坡,时常有蛇等小野生动物出没,养有鸡鸭,植有20多棵果树,有10多种南方水果及瓜菜,随时都有水果吃,吃不了的每年还能卖些钱。家里养有狗和猫,狗看家护院,猫经常在后院抓只老鼠、蛇、鸟或什么虫子在家里玩,不吃,玩死了就放在墙角不管了……
我结婚那年,带着北京媳妇探家。记得刚到家,父亲给煮粥喝,见吃的咸菜很特别,问我是何物做的,我说是芒果,她很惊讶(那时北京很少卖,十几元一斤)。看到家乡山清水秀高兴;见到粗大的石竹高兴;看到橡胶林高兴,照相,假模假样的当回橡胶女,乐不思返。
女儿尧尧两岁时第一次回老家,从北京到广州好好的,从广州到老家一上火车大哭不停,谁劝也不行,快到那霍站时哭泣得更大。到站下车,我母亲抢过尧尧就抱着,尧尧立即不哭了,我母亲抱着尧尧,不停地亲着尧尧,尧尧双手搂着她阿婆脖子不放,从车站到家不放手,其他人谁抱都不行,搂着阿婆紧紧地,小脸亲着阿婆的老脸,让在场的所有人感动和不解,这可是祖孙二人第一次见面!
尧尧第一次见到遍野的含羞草好奇,第一次回到老家见什么都高兴,饿了就到后院,上树摘水果,吃个够。
尧尧的舅舅也跟随回了老家一趟,玩了5天,吃了5天家乡饭,明白了什么是正宗的广东岭南客家菜,长了5斤肉,赶紧先返京了。
我探家次数不多,但每回去一次,感受都不同,心情都很复杂。一是见70多岁的父母亲老了许多,作为儿子,又不能尽赡养义务,心里内疚。二是看着自己的家还是那样变化不大,自己无为,心里歉疚。
父亲在家乡解放后不久就参军去了,听母亲说是结婚以后参的军,走后好几年才回家一次,父亲30多岁才生的我,是母亲在家乡将我带大的,那时候家里生活很苦。在我4岁之前的记忆中,没有父亲的概念。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带着我到“北方”探亲,记忆中的第一次和母亲到部队探亲好像是到武汉,后来得知是住在武汉钢铁厂附属医院。当时正是**期间,父亲是驻厂军代表。当年,父亲所在部队是武汉军区空军第十五军空降部队。
我实在是记不清几岁到的武汉,只记得常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的砂堆上玩。住的是楼房,而且有电梯。有次与一名小朋友开电梯玩,不知按错了哪个键,电梯卡在楼层之间不动了,两人在电梯间里大哭,急得母亲楼上楼下的乱叫,从白天到天黑,大人们忙碌了大半天才从电梯箱里将我们拉上来。过去快40年了,母亲提起此事还后怕,见到电梯就两腿哆嗦,一再提醒我今后买房,千万不要有电梯的。
那时候,常有高音喇叭的汽车在大街上来回跑。隔几天就有军车押着要枪毙的死犯经对医院门口的大街,犯人被绑在卡车前帮上,后脖颈插着牌,胸前还挂着牌,写着什么罪,名字上面画个大红叉,死犯个个看上去面目可憎,给我印象最可怕的是一些从口中吐出舌头的犯人了,身后左右各有一名拿枪的军人押着,车上还站着两排拿枪的军人,表情严肃。车子慢慢地开着,在车队的前面有一辆广播车,不停地说某某犯了什么罪,判处死刑……。街道两旁围观的人很多,只是静静的看着,车队过去了,人们也散去了,街道又恢复了原来的喧闹。
有时大人们也带我上街,看到飘在空中的气球好生奇怪――为什么我吹的气球就飘不起来呢?
父母带我参观过一个教育展,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大地主刘文彩的罪行展,印象很深,后来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中有这篇课文。
还记得有几桩淘气的小糗事:因好奇将一支不出水的圆珠笔芯油墨吸进肚子里,恶心了好几天;上厕所不小心将一支叔叔送的新钢笔掉进了茅坑,伤心了好几天;有一次在院内砂堆玩耍,正玩到兴头上,附近锅炉房的开水锅炉突然爆炸了,吓了好几天;还有一次母亲让我热牛奶,由于贪玩忘了牛奶烧干了,把锅也烧毁了,母亲骂了我好几天……
也有高兴的事儿,每天都能吃饱饭,不用饿着;吃了些我从没吃过的水果;还有牛奶、点心等。第一次进大城市,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见到高楼,第一次住进楼房,并乘过电梯,还有很多的第一次……如:第一次知道电灯,一拉绳子就亮;知道什么是水龙头,只要一拧开关就出水。当时想:这若是能安在老家的房子里多好啊!
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是母亲带我去北方探望父亲。那时我还很小,实在不懂事,在火车上我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大声叫喊着要吃鸡腿,吵闹了不知多长时间才得到。现在,每当母亲提起此事,老泪在眼睛里打转,可想当时这事对母亲来说是很棘手、很为难的。长大了,懂点事了,心里想起,总感觉对不起母亲,现在我一看见鸡腿就犯怵。
记不清随母亲有多少次到部队探亲。有时有父亲陪着,一次,父亲带着我们在中途下了火车,就住在铁路旁的平房里。晚上,火车轰鸣声、气笛声,阵阵入耳,难以入睡。天未亮大人把我叫醒,草草地吃了早点,就摸黑上了火车。
后来长大了点才知道那是广西玉林火车站,住在王叔叔家。王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记得我家搬在湖北云梦隔卜武空1114盐厂时,王叔叔多次来探望,并且带来很多糖果,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就是他给我的(那巧克力的香甜口味实在是印象太深了)。有一年我探家,王叔叔还来看我,他已退休了,老了很多,但还是显得很亲切,他说还是住在玉林火车站,我总想有一天要去探望他老人家。
还记得一次父亲送我们返回家乡途中,火车在一个小车站停下,父亲下车给我们买水果,结果火车停的时间短,父亲没上车,火车就开走了,急得我大哭,母亲更是急,与列车长联系,在下一站就下了车等着父亲。后来父亲是延着铁路走来的。我们在车站的安排下坐了一列路过的货车,在尾部小车箱里坐到终点站。长大后母亲告诉我,父亲下车的车站是河唇站,父亲见车站有荔枝卖就下车去买,结果误了时间。
当年,由于交通不便,每次探亲路线图是这样的:从石牌垌走到黄岭,坐汽车到水东,在水东大伯家住几天,再坐汽车到湛江,然后再坐火车到父亲服役部队所在地附近的火车站,坐汽车到驻地。返回家大多是坐火车到湛江或茂名站后坐长途车到水东,在大伯家住几天后再坐车回黄岭,从黄岭走回石牌垌。这对母亲来说,一个南方没有文化而且方言不通(我是讲涯话佬)的农村妇女带着孩子到北方探亲是很辛苦的,何况母亲患有严重的晕车症。
我的母亲晕车很严重,有时像要虚脱的样子。我也晕车,一坐车就难受。我的女儿尧尧也晕车,有一次坐飞机,脸煞白,胃里的胆汁都吐出来了,这也许是遗传。
我小时与母亲在老家生活,期间有几次到父亲部队探亲,长到7、8岁才正式离开家乡,随军到湖北省应山县广水公社,在部队驻地那儿一个小山村的小学上学。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搬到湖北省云梦县隔卜公社,住武汉空军1114盐厂,在隔卜公社上学,至1979年高中毕业,年底参军到北京。1982年初利用在外学习放寒假期间探家,回老家过的春节,这是我离开家乡12年后的第一次探家,时年20岁。记得那次探家,没让家人接站,凭着儿时的记忆,准确“摸”回老家,着实让父母及亲友惊喜,少小离家,回来已是个壮小伙子,家人当然高兴,此后每年都要探次家。结婚后因为各种原因,探家就少了,这是我心中一个理不清的结。
离开家乡时虽说还小,但家乡给我儿时留下很多美好记忆,这记忆是永恒的,这记忆是深刻的,这记忆难以忘怀,这感情难以表达。
我的家乡是广东省电白县黄岭公社水西大队石牌垌生产队――这是当年的称呼,现在全称: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黄岭镇水西管区石牌垌村。
我出生在贫农家庭,长在农村。虽说父亲是军人,但父亲远离家乡在外地服役,家里的事关照不上。所以,我基本上是母亲带大的。
母亲说我是很有福的孩子,吃母乳到一岁大,小时候白白胖胖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母亲的话是可信的,每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付出最多,对自己孩子都是赞美的,认为自己孩子是最好的。何况当年父亲不在身边,只有母亲带我,当年生活很苦,把我带大不容易。所以,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
我的父辈排行是这样的:我父亲老大,两个姑妈在中间,幺叔最小。我不知母亲有多少兄弟姐妹,每次探家我都犯晕。后来看家谱,因只记男不记女,很多亲戚无从核实,这就不说了。
我阿婆瘦高个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头,头顶掉光了头发,边上的头发稀薄没几根,并时常头痛,头皮是花的,有疤痕。听大人们讲,阿婆年轻时,有一次在地主的地里干活,因故被打,一锒头打在脑门,差点死了,从此头就这样了,没法治。我长大点,记得父亲多次找医生看,没治好。
年幼时,母亲背着我下地干活;年少时,母亲出工,阿婆就带我。阿婆没有留下张照片,30多年了,她的模样已淡去。她带我到8岁;也带过我大弟汉平,那时汉平还小,想必没什么印象;没带过小弟爱民,他就不知道阿婆什么样了。
阿婆好像是在我10岁左右去世的,当时我家在湖北省应山县广水公社很远的一个山坡军营里,当年父亲是武空15军应山飞机场地勤汽车连指导员。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阿婆死了,母亲眼泪出来了,我听了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父亲一人探家料理后事,记得那是5、6月的季节,父亲从老家回来时带了很多家乡的水果。
我没见过爷爷,母亲说她嫁到这儿就没见到,说明爷爷死的早,父亲从没给我讲过爷爷的事。听大人们讲,我爷爷是个有点文化的人,当过私塾先生,所以家里有很多的书,我小时不懂事,因为好奇,又没什么好玩的,就偷偷地拆毁过很多爷爷遗留下的书,那些书都是线装的,很精致。我后来探家时总想找这些书,没了,一代穷书生,其后人没几个读书像样儿的,可叹!
我幺叔是我最亲近的人,在我年幼时,幺叔很疼爱我,时常护着我,时常带我玩耍。如做风筝、捕青蛙、采野果,背我过看病……,我父亲不在家,他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是顶梁柱,是我靠山和依托。
幺叔生有三男二女,我在家乡时,已有大堂妹和两个堂弟,后来两人是我到“北方”后出生的,就不熟了。我第一次探家时,大堂妹已出嫁到邻村的一户人家,其丈夫当过兵很能干,一家生活水平在当地还算可以,建了楼房。最近几次探家,只见二堂弟在家守着老宅种地,老实本份。幺叔和另外两个堂弟在阳江市以养鱼为生。
姑妈家住高州县龙潭公社,我有一表姐三表弟,其中一个表弟阿狗仔是个残疾儿,与汉平同岁。当年姑妈很疼爱我,母亲常带我去探亲,因为路走熟了,有时我自己一个人就去了。有一次,傍晚我一人走到姑妈家,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吓得我直哆嗦,但还是因为饥饿战胜了恐惧。为了一碗饭,把家人都吓坏了。现在姑妈家搬到高州市,在市里建有六层小楼,一家生活都很不错。
我外公瘦小个子,精神很好,主要特点是他有几根眉毛特别长,人称长寿眉。人总是乐呵呵地,爱说爱笑,人很勤快,能干。对我很好,小时母亲常带我去外公家探亲,外公家做的饼很好吃,外公家座落在罗坑公社的一个小山村,要走很长的路,趟几条小河,翻过几座小山丘,路过好几个村庄。村庄坐落在一个山丘上,外公家门前有一口井、一片小竹林、一个不大的水塘。幺舅带我和表弟、表妹们到附近的山野玩耍,记得村边有一很大很长的引水渠,我们在那儿抓过鱼虾。
听母亲说,外公结过两次婚,母亲是长女,亲外婆很早就去世了,母亲是跟着后外婆长大的……。关于她儿时在娘家的事,零零星星的,她说的不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她对外公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好。我母亲是敢说敢干敢恨敢爱的人,内心有什么事都表现出来。但作为女儿,对其父亲还是很孝敬的。
外公身体很健康,我探家时,他80多岁了有时能走很长的山路到我家来。外公是2003年去世的,享年??多岁,去世时亲戚告诉我父亲,我父亲不信,下葬后的次日才知道是“真”死了,一个人才跑到坟头跪下大哭,成了大家的笑柄。这说明外公生前一直是很健康的,去世前后没有给家人带来麻烦。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城里来了一位非常漂亮的阿姨。到村里来教大人识字,并教大人唱歌。那时,母亲常抱着我去上课,这个阿姨在我印象中长得是最漂亮了,与这里的村姑反差很大,白净透红的皮肤、粗长黑亮的辫子,大大的眼睛,漂亮的衣服,高贵的气质,和蔼的神态,我从没见过,说话很好听,和广播电台一样的声音,宏亮并且听起来甜甜的。她走到哪儿,总有一大群小孩子(也有我)跟在她后面,村民总是围着她说些家长哩短……她总是笑着,不知为什么她总是有那么多的高兴事儿。她是哪儿人?从哪儿来?无亲无故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至今也不知,也没问过。
这个阿姨与我母亲同姓周,日子长了与我母亲成了好姐妹,她时常给我些吃的。后来她走了,到黄岭公社饭店工作。走后,母亲常念到她,有时带我去过探望她,在我印象中,只知道周阿姨那儿有饭吃,所以,我有时饿极了就自个一人走10多公里山路到黄岭找周阿姨,住上几天,吃饱喝足了才回家,搞得家人很不好意思。过了一年左右,周阿姨离开了黄岭,不知道又到哪儿去了,再也没见面,我时常想念她。
所以我参军后的第一次探家,一回到家乡即刻到处打听周阿姨的下落。自从周阿姨离开了黄岭,大人之间就没再联系过,好几天才得知她在茂名石油公司工作,我即刻去探望她。她与十几年前比,变化很大,老了许多,发福了许多,差点认不出来。没变的是她还是那样美丽,依然显得气质高贵,并增添了几份慈祥。
第一次见面,周阿姨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实在是感动(女孩很漂亮,是羊角公社人,与她见过一次面通过几封信后再没来往)。
我家乡位于广东省西南山区,靠海,北回归线以南,受亚热带海洋气候影响,四季不分明,而分旱季雨季。在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雷电轰鸣,常有台风经过,暴雨成灾。旱季雨水不多,但河溪水流不断,一年总是绿油油的。家乡是丘陵地带,红土地,山不高,水不深。家乡离大海约有40多公里的山路,村离县城水东镇有90多公里。我的家宅位于村东南隅,土砖墙,青瓦房,是典型的广东岭南农舍,正房中间为厅,侧房住人,两侧厢房设有橱房、杂物间、耕牛棚、或放些农具、农物、柴草等,中间有个大天井,正门朝东,门前有一猪棚,一水塘,一条小溪,小溪里有小鱼虾,并时常也有毒蛇出没。村子里有很多的果树,龙眼、荔枝、波萝密等南方水果。村和村之间很近,人多地少。农作物以水稻为主,种两季水稻,因雨水多,田里小鱼虾也多,青蛙也多,成天叫个不停,时常夜里幺叔带我去田里抓青蛙。离村不远有一条河,因我村在河西岸,所以村所在的地方叫水西,归黄岭公社。河对面叫水石,属于那霍公社。大人们常在河里抓鱼,小孩子常在河里游泳或在河滩放牛、玩耍。
村口与河之间有条小路相通,路边竖有一石头,像块石牌,孤伶伶插在土里,露出地面一人多高,所以我村名叫石牌垌。
相传,这石牌是我村的象征,是福祉,是命根,有很多动人的古老传说。此石牌有仙气,常被他人偷盗。相传很久以前,一次石牌被妖魔偷走,全村老少奋力相争,夺回石牌,再次立于村口,村民日月守护着,至今依然屹立在哪儿巍然不动,守望村民的出行,保佑村民的平安。在我儿时,这石牌边有村口通往河边的小路,我走亲访友,后来上学都路过,有时在石牌边玩耍,在儿时的心目中,这石牌是神圣的,同时又显得非常神秘。也许我那时还小,大人们没有给我讲过这石牌的来历,这石牌是什么?为什么会孤伶伶地立在那里?
以前村民出行有三条比较宽点的泥土路,一条到黄岭,一条延着河边到高洲的龙潭(一段泥土路、一段柏油路即广州至高州省级公路,也可到那霍),一条就是走石牌边的小路过河到那霍,(另有很多已记不清的山间“小路”,我到龙潭姑妈家走的就是这种小路)。现在人们外出走路的不多了,经济发展各种车辆的使用,村民就很少再走石牌这条路了,石牌周围变成了农田,所以这条路也就没了。现在的村民要到河边很不方便,只能走弯曲的田埂。
村前的河,大人说以前常犯水患,约在我5、6岁那年,政府出资,动员沿岸百姓清理河道、加固堤坝、疏通河水。那时青壮年劳力都参与到了这劳动大军中,只见河的两岸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幺叔也给我做了个小扁担和一对小箩筐,带我到工地,从河中挑卵石到堤坝上。天天都去,我也争工分。那时干活很苦,不是暴晒就是雨淋,工地上没遮没挡,在工地也有少年参加,然而像我这么小的孩子也就我一个。那时我小,挑担子晃晃悠悠,为此闹出不少笑话。从那时起也就和母亲一起下地出工了,成了个小社员,挣工分。后来上小学,课余没事也常下地干活或帮家里做些家务。
已过去30多年了,长辈们见到我就常提起当年此事,而母亲在一旁总是伤心的样子,眼里含着泪,有时冲着人们大声嚷几句,然后独自一旁沉默不语。
一次探家,与母亲一起路过这条河,她停下来站在堤坝上,拉着我的手,看着流淌的河水,老泪也流到了她老脸上,说着一些过去伤心的话,母亲好像对我一辈子都很愧疚,好像让我受了不少苦。这就是我的母亲,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当年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丈夫不在家,过日子是很难的,她所受的苦能对谁说?谁能知道?谁能分担?
我每次探家,一是必看石牌,二是必看这条河。这条河给了我童年快乐,也给了我童年许多磨难。河水始终都是清澈见底,鱼虾在河床下的鹅卵石间漫游,翠绿的河滩如同铺了一层草甸,河边有不停转动的水车,时常见人赶着一群鸭、鹅从河面经过,儿时常与小伙伴在这条河一起放牛、玩耍、游泳、抓鱼虾,渡过每一个快乐时光;而这条河也让我流过汗水,让我母亲铭刻着苦的记忆。这条河现状与儿时大不一样了,现在除了河水还是哪样清澈外,鱼虾已不多了,也很少见村童在河里戏耍,以前得趟着过河,现在河上架了一座简易木桥,桥头有收费的,半天见不到要过河的行人。
小时候常跟着母亲走亲戚,大多要过村前的河,过河后还要走好长的路,有的还要翻山越岭。记得深刻的山路是到铁打水姑妈家。铁打水座落在一高山的山坳里,山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清澈的溪水潺潺不断,飞禽走兽,花草鱼虫,山珍野果,山水如画,一派热带雨林景象,如同人间仙境。村子不大,与其它村子相隔很远。儿时姑妈家那儿养有梅花鹿,野猪常到村边骚扰。表哥常在村后的沼泽地里插些树桩子,没几日就长出很多的木耳,做菜很好吃。当年,这儿对我没什么好的印象,因为要走一整天的山路,从一大早出门,下午才到,累!特别是到了晚上,感觉是阴森森的非常可怕,但是,我每次去那儿都能吃上很多的山珍、野果、蜂蜜什么的,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条路线是这样的:出家门、过河、过水石、过那霍、再过条河、穿过几个小山村,路上有一小水库,漫长而又弯弯的山路。我小时候没敢独自一个人走这条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村民进出不便,路人很少,至今也没能通车。
儿时,母亲说要走亲戚,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不让背,自个走得欢实着呢。
那时,只要大人带我走过一次的路,都能记得,只要目的地有好吃的,就记得更清楚。为了吃的,一人走到黄岭找周阿姨,吃饱后再住上几天才独自回家。一人走到龙潭姑妈家,玩几天,玩够了才回家,哪怕是走夜路。这样的事不止几次,那时候母亲白天出工了,家里没得吃的,肚子饿,有时告诉阿婆一声就走了。我知道哪条路好走,哪条路目的地有什么吃的,只要有好吃的,哪儿我都敢去,无需跟大人走。
我年幼时,晚上母亲有时对我说很多话,有很多我听不懂,但很愿意听母亲讲故事。讲的都是些鬼神,一是水鬼,二是山鬼,都是吃人的鬼,讲得很多,讲得很经典,我还记得一些,其内容从古至今没有书记载,在我上中学时曾经整理过,后来因多次搬家等原因,书稿早已不见。
母亲说我是从河边的草地上拣回来的,我信了,后来有了弟弟,才知道母亲说的不对。
母亲说她年轻时在砖厂干过,在水泥厂干过,后来嫁到这里,当妇女队长。母亲很勤快,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在我记忆中,母亲好像没觉得累的时候,母亲心地善良,性格泼辣耿直,敢说敢干。
幼儿时,我常在家里的土地面上爬滚玩耍,沾得满身鸡屎狗屎,我头上、屁股、身子、腿脚上长了很多的脓泡,苍蝇在脓泡疤口上爬来爬去,赶都赶不走,现在全身还留着很多这些疤痕,这是我1、2岁时给我留下仅有的记忆。大人说:我幼儿时鼻涕流到下巴,也不擤,这事常成为大人的笑话。
4岁大时,走到一个粪池边时,不小心掉到粪池里,呛了不少粪汤,好久大人才发现,大人们是怎样把我拉上来记不得了。醒来时只知我爬在地上一口倒扣着的大铁锅上面吐粪汤,幺叔看我清醒过来了就抱回家。家人给我冲洗了好久,我不停地哭,阿婆不停地骂着母亲,母亲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给我洗身子,让我喝了好几大碗药汤,上吐下泻了好久。第二天阿婆见家里实在没什么吃的,就让堂妹陪着我,拿个大竹筒,在附近村子里挨家挨户讨些米回来,煮稀粥吃了好几天。这就是我要饭的经历,终身难忘。
最让母亲伤心的,而是在我5岁左右大时得了一场大病。后来听母亲说,我当时发高烧42度有好几天昏迷不醒,母亲到处请大夫,都没法治,有人劝我母亲放弃。深夜病情加重时,母亲一人摸黑背着我到水石看医生,那医生给我打了针,灌了药,很久不见效,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没救了,准备后事吧。母亲急了,说无论如何也要治好孩子病。母亲要了些药,深夜又背着我往回赶。水石与我村有十多里路程,之间还隔着一条河,水流很急。但母亲还是以最快速度赶回家(这条路我走过,白天走都很难,深夜里一个女人背着个5岁大的病孩走这路不可想象),回到家叫醒幺叔,让幺叔背着我到黄岭公社医院,在医院住了十几天。我记得,当我醒来时第一句话是:阿妈,我要吃酱油泡饭。对我来说,这是最好吃的了,虽说味道与我平时吃的有所不同,可能是因生病,舌头味觉并没有感到有多香。病好后,幺叔就背着我回家了。到家时,放我下地,看到幺叔后背湿透了,不像是汗,一闻才知是我尿的尿。
那时,我已很久没让大人背我了,因为我自认为也是大人,之前我背过堂妹、堂弟。这次让幺叔背了,还在他后背尿尿,感到脸红。这场大病差点要了我的命,不是母亲的坚持,也许我就没了。幺叔一家也为此着急,让我一生感激不尽……
从那以后,除了胃有点毛病,并时常脑子有点犯晕,其它的我没再生过大病。
我父与幺叔虽说分了家,但两家还是住在祖父留下的屋子里,阿婆也和我们一起住,实际上还是一个家。后来我家随军后,屋宅由幺叔住了,幺叔赡养阿婆,并送终。我家在当地还是比较不错的人家,每隔一段日子,父亲总能寄回些钱和粮票、布票什么的,但每次到北方探亲这么来回一趟,几年的积蓄“都交给了铁道部”(母亲语)。在当年,村民生活都很苦,收割粮食后交公粮,生产队留下的就不多了,年底分红,每户分不到多少粮食,折算下来工分也就几分钱一天。
正因为当年家乡生活太苦,交通闭塞,人多地少,物资匮乏,村民终日为衣饱所愁。所以很多村民在外谋生能在外安家定居的,不愿再回家乡。我家随军在湖北定居后,父母就不愿让我再回去,也不愿提家乡的事,除了因阿婆去世,父亲独自回去料理后事外,全家十多年没探过家,至到1979年大栽军,父亲转业不得以才回家乡,但还是不让我跟回去,让我参军远离家乡。
听母亲说,在我还没出生前的那几年,没吃的,树皮都吃光了,那个村都要饿死不少人。后来政策有所变化,日子才有点好转,至少逢年过节偶尔还能吃上一两顿饭。当时虽说每户人家有几分自由地,种点菜、养些鸡鸭猪什么的,但还是很苦,煮的粥都能数得清米粒,大多是番薯就咸菜,时常为一日柴米油盐发愁。
有两三次晚上,随幺婶一起上山偷过柴(那时的山、田都属于生产队的)。晚上在山里走好远,黑灯瞎火的,割几镰刀就赶紧帮,挑起担子就往山下跑。那时没鞋子穿,光着脚,回到家时,脚掌扎了好几个洞,痛也不敢叫,实在受不了,再说这人群中,就我一个小孩子,母亲也反对我去,两三次后再也不去。然而,生产队分的那点柴,绝对不够烧的,无奈,只好白天到田埂、沟壑旁割些草回来当柴用。
我是6岁上的学。学校是什么样子就不说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的小学校比我们学校好多了,那儿毕竟还有桌凳,我们连桌凳都没有,下雨时屋里比屋外下得还欢。
在家乡上学的记忆不多,只记得一年级第一堂课,老师就教我们写5个字“毛主席万岁”,歪歪扭扭地,放学跑回家拿给母亲看,会写字了,高兴,后来又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我的小学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几次到“北方”探亲,随军后在当地农村学校上学,由于方言差别太大,老师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老师和同学都听不懂并取笑我。一、二年级就没怎么正经上,不得不复读二年级。实际上,我在小学没学到什么。特别是语文课,可以说就没学,一上语文课就头痛,见拼音就晕,所以我至今还是吐字不清,发音不准,在正规场所发言就脸红、流汗、哆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毛病有所好转。但写个文字材料总是语句不通,错字连篇,表达能力差,这辈子不会有进步了。
我的爷爷是个书生,父亲上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母亲从没上过学,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的就认得银纸(方言:即现金钞票)上的数字了。在我很小时候,周阿姨来到我村,教大人识字唱歌,母亲很积极,每堂课都去,但除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其它的也没学到什么。
……
儿时的记忆还有许多快乐事。
最高兴的莫过于过年了,有新衣、有好吃、有炮放、有戏看、走亲戚、与小伙伴玩游戏……。人们于节前就准备着直到元宵节,都在忙碌着快乐着。过年时每家每户都早早地备着鸡鸭鱼肉,放在祠堂祖先牌位前,全家人在祭台上点蜡烛、燃香、鞠躬,祭祀祖先,然后许个愿,亲人相互说些祝福的话。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长辈给晚辈发红包,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或放炮竹,或说旧年中的家长里短、展望新年前景,或玩牌游戏,其乐融融,守夜等待着新一年的到来,寄望着新年带来好运。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早早地起床,打开家门,放鞭炮,邻里乡亲互祝新年。过年时家家都做“鸭麻圆”吃(即汤元,无馅、用老母鸭顿汤煮,特香,是典型的岭南客家风味),并做些饼以备走亲访友时相互赠送。连续十来天都是走亲访友或亲戚来探,好不热闹。有时有舞狮队来门前表演,锣鼓喧天,这时,家主人拿一红包悬挂在高高的屋檐下,顿时只见瑞狮高昂着头,舞动着身躯,慢慢地靠近红包,用嘴衔着红包取下来,向主人示谢意,对瑞狮的表演,围观的人们报以掌声,红包中的钱不在多少(有时红包里放的是饼什么的),大家都是图个乐。
说起热闹事,印象深的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村里的人家娶媳妇,那气氛就像是全村的喜事一样,小孩子们都跑去看新娘,抢喜糖,好不热闹。
另一个是鱼塘起鱼,当年鱼塘都是生产队的,打起的鱼家家都有份。大人们头几天就准备了,当天只见男人在水塘里下网打鱼,鱼在塘里跳跃,岸上的人们笑逐颜开,女人拿来盛鱼的家什,小孩子在水塘岸边帮着大人抓鱼,人们欢叫着,开始称鱼分鱼,末了每家都拿着分到的鱼回家,晚上,全村弥漫着家家户户做的鱼香味,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有好吃的就高兴。
清明节,大人带着小孩子扫墓祭祖,是必做的,接着就是一年农忙正式开始了。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做很多的粽子,四棱的、长条的,形状各异;大多是肉馅的,味道各异,很好吃。走亲访友时相互尊送,能吃很长时间。
还有一个重要节日是中秋节,月饼是最好吃的,农家自己做,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五花八门,各家品味各不相同,既好吃又好看,口感香甜。现在再好再贵的月饼也不如那时的好吃,遗憾的是再也吃不上了。
再有就是与小伙伴到水田、溪河、水塘里抓鱼虾,捕青蛙,还经常到河里游泳,到已收割田里拣稻穗,进山里采野果……。
每年春夏季有很多水果吃:龙眼、荔枝、波箩、芒果、香蕉……品种很多,虽不是随便就能吃得上,但总能吃个够。
晚稻收割后,开阔的田野就是我们孩子放风筝的天地,风筝都是自己做的,造型简单,图案素雅,用竹条做龙骨,糊上纸,后背再绑上个竹片弓,风一吹就响。人们比着谁的风筝大,比谁的风筝好看,比谁的风筝声音响亮好听,比谁放飞的高、飞的远,比着放飞心情、放飞快乐。有时天上风筝发出的声音很响亮,传得很远,这是我家乡独有的,北方人不会做,我在北方30多年从未见到。
……
以上是我儿时在家乡的部分记忆,随着时光的流失,很多记忆已逐渐淡去。
现在的家乡变化很大,虽然与广东其他地区比有些差距,但与过去比还是有进步,生活水平提高了,楼房多了,果园多了,路好走了,汽车多了。我离开家乡在外谋生,很惭愧不能为家乡建设做点什么。
石牌垌变了,但很多老人没了,儿时的小伙伴变成中年人了,不认识村里的青少年了。山上的橡胶林少了,深山里的大树没了,河鱼没以前多了,田里的青蛙很少见了,以前哪不分男女的路边厕所没了,村民见什么吃什么的习惯也改了,小学校园也变了……。不变的有我儿时说的家乡方言土语(涯话),不管何时何地,家乡话总是那么亲切,永生难忘!不变的还有记忆中的老宅、老井、水塘、小溪、河水;还有那永远不变的碧水蓝天以及永远淳朴的民风……特别是村口那座石牌,她还是哪样静静地孤伶伶地立在哪儿。像是站在村口守望游子归来的老人,任凭风吹雨淋日晒,日日夜夜总是巍然屹立在那儿,告诉外出谋生闯荡的村民:有亲人在惦记,有神灵在保佑;使游子不会孤独,不会迷失。我是她的游子,自幼随父母远离家乡在外谋生,成年后又独自在京城做事,生活习惯已改变,儿时记忆已淡去,但石牌依然在我心中,永远还是那样既神秘又神圣。
我每当怀念家乡时,就想起这石牌和村前的河,童年记忆总是显得很美好并充满着梦想,同时也因为我出生在这如此美丽的家乡而感到自豪。这就是我的家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走到哪儿我总是怀念她、赞美她。她在我心中总是哪样伟大、慈祥。我的祖祖辈辈在这儿生生不息,感激她养育过我,儿时的记忆在我心中永恒。我衷心地祝愿她越变越美丽、越变越富饶!我永远地祝福她!